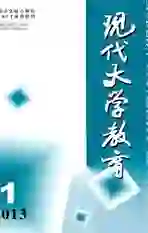功利意识、道德分化与排他性的教育伦理生活
2013-03-29吕寿伟
吕寿伟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便逐步完成了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一方面通过功利意识遮蔽着真实的教育伦理生活,另一方面通过道德的领域分化和公私分离使个体将良知封存于内心。无论是功利意识还是道德分化都导向了教育生活中排他性的自我关注。然而,伦理之为伦理就在于它总是超越自我利益而表达出对他者的尊重和重视。教育生活的自我关注不可避免的阻碍了自我对他人伦理要求的实现,同时也自然的放弃了自我对他人的伦理责任,教育伦理生活也在排他性利益的追求中走向了去伦理化的道路。
关键词:教育伦理生活;功利意识;道德分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1-0092-06
教育伦理生活简单的说就是在特定的教育共同体中依据一定的教育伦理规范形成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往的方式和生活的秩序。教育伦理生活不具有独立性和自身的可感性空间领域,而是依附于符合必然性法则的教育生活而存在,所谓教育的必然性法则是指教育活动所要遵从的内在规律,如学生的认知规律等。完整的教育生活是必然性生活和伦理生活的统一,既不存在纯粹的必然性教育生活,也不存在纯粹的教育伦理生活。这便决定了教育伦理生活的实际存在样式在为教育伦理生活自身的价值规范所限定的同时,也取决于必然性生活的性质特征,寓于必然性教育生活中的支配性的价值观念的选择将对教育伦理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教育伦理生活在内涵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教育伦理生活的狭义概念,指具有合伦理性的生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善的,在存在形态上表现为应然性,应然的教育伦理生活具有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它通过伦理价值和伦理规范实现对教育生活的价值引领,使教育生活朝向善的和正当的方向迈进,因此是规范性的;二是伦理生活的广义概念,仅指具有伦理属性的生活,表达的是教育生活的客观状态和实然特征,实然的教育伦理生活为我们日常所面对,并直接关涉个体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虽具有伦理属性,却并不一定合伦理性,即实然的教育伦理生活是经验性的,在其现实性上并不必然表现为善的或正当的。
伦理生活研究就是通过对实然伦理生活现象的关注,解释其形成原因,论证其合理性基础,并提出伦理生活的当然之则,使伦理生活指向应然的价值诉求。[1]既然为我们日常所面对的教育伦理生活往往并不必然是合理的和完善的,便有必要对为我们日常所面对的当前的教育伦理生活的真实处境做出分析。在此,本文将依据对教育生活之必然性和伦理性的划分,并立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2],分析、揭示实然存在的教育伦理生活的当前状况。
一、功利意识对教育伦理生活的遮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便逐步完成了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市场的逻辑在于为进入市场的所有人提供服务,然这种服务的提供是以经济支付能力为依据的,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们所获得的福祉永远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市场一方面通过各种令人神往的服务无限膨胀着人们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激励着人们通过劳动来占有和享受各种服务的支付能力。欲望就取代精神的向往和价值的追寻成为自我意识的起点,[4]欲望、劳动、占有和享受成为市场驱使下的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将自我意识确定为对财富、消费等功利性目标的占有,并将财产等确定为自我不变的本质。然而,在功利意识把这些具体的有限性作为自己的规定特征的同时,个体也把自我抛散为一切特殊性。功利意识通过劳动、享受和占有来满足着自我的确证,这种暂时性的自我确证使自我在占有的快乐中掩藏了内在苦恼意识,反而将自身装扮为快乐。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人就降格为某物,因为他失去了本来所有的自决性而成为某种被决定被操纵的东西。”[5]市场通过功利目标使生活遵循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法则,而忽视生活的伦理属性,它通过个体交往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着对伦理生活的遮蔽。在市场经济中交往依然不可避免,但交往的对象、交往的目的和交往的内容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市场中交往是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与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商品交换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样的交往并非是源于内心对摆脱孤立状态的渴望,而是源于功利目标的驱动以及不可逃避的市场力量的逼迫。交往的目的不是达成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而走向了个体的自我关注,使自我的私人生活成为最终目标。尽管此时交往依然不可避免,但是此时的交往只是基于必然性的交往。因此,基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我们不难理解功利意识的伦理生活只是以特殊性为原则的生活,并通过对无限的遗弃使真实的伦理生活遭到遮蔽,功利意识的伦理生活不能使自我获得完善。因为,此时自我只是把伦理规定为私人利益,只有在这种对私人利益的占有中才能获得真实性。但伦理生活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统一,在于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伦理生活的本质是“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6]
在功利取向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这一永不停息的“隐藏运作”系统[7]将功利目标渗透于各个领域,教育也不得不将自身卷入市场以适应时代的状况。如此,教育便走向了适应市场的路径,而放弃了教育自身的价值,以及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衡量教育优劣的标准在于教育对于社会功利目标(尤其是经济目标)实现的程度。教育不再是因为自身的独特性以及对人的发展的促进功能而存在,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工具而存在。作为工具的教育不仅体现在教育自身对于社会的工具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自身成为将人塑造成工具的工具,它“教人去追逐、适应和改造世界,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但它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8]教育被需要是因为教育有助于获得最大化的功利,如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言[9]:
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系……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
功利化的社会在对教育进行改造的同时,也不断的重塑着教育伦理生活。既然教育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体面的工作和相应的社会地位,那么自我的全部努力便为着这一私人的目标。人的确需要目标,甚至人之所以是自由的、之所以是高于一切纯粹自然之物或野性之物,恰在于目标的设定[10]。然而,当私人目标被抬到首位时,教育也就成了自我关涉的活动:尽管自我与他人共处一室,但他者的存在对我而言只是如车厢中乘客之间的偶遇,每个人都专注于自我目标的实现,彼此之间鲜有共同的关注,每个人都似乎很情愿保持这份乘客式的和睦;尽管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合作,但这种合作就像是车间中的分工,合作的目的在于学习任务的更好完成,从而更好的达成个人的目标,合作只是教育内在必然性支配下活动,它可以增加教育的效率,却丝毫不能增加教育的伦理属性。于是,自我在功利目标的引领下日益孤立化,自我与他者相伴、相处,却无道德上的共契与伦理的相依。生活的私人化使每一个个体都将自身锁闭在一己的私人领地而放弃了生活的伦理追求。自我虽生活在班级、学校等伦理实体内,但却因关系的断裂、公共性的丧失而脱离真实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伦理实体,从而失去了伦理生活。因此,依附于必然性教育生活而存在的教育伦理生活便因为功利导向下的教育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否定而遭到彻底的遮蔽。
功利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教育领域获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是因为它一方面通过无限膨胀个人的欲望而使个体放弃生活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功利意识通过自身的运行逻辑以及隐性的规则强迫或诱惑使个人进入功利社会主导下的必然性生活之中。但生活不仅是必然的,同时也是自由的[11]。教育生活也不单纯是满足学生认知规律以及教育内在运行秩序的必然性生活,同时是有人的自由意志参与的自由的生活,即伦理生活[12]。功利意识的后果在于通过预设的功利目标将教育生活简化为学习生活,将受教育过程简化为知识和知性能力的积累过程,以使个体能够避免在未来遭遇物质匮乏的生活,或者使个体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从而不仅避免艰苦的生活,同时还能够体面的享受生活。因此,功利导向下的教育目的在于满足受教育者的谋生和享受的欲望[13](而享受也并没有改变谋生功能内在的物性生存的本性)。然而教育从来不是为了单纯的物性生存而存在,而是要通过伦理性的治理而实现个体德性的教化、人性的完满。[14]因此,教育生活首先是一种伦理生活,而功利主义教育为了生活的改善,却最终在根本上放弃了生活。因为,在功利目标驱使下,受教育者日益走向了生活的自我关注,形成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的教育生活方式,从而导向教育生活的私人化与孤立化,引发教育中伦理关系的断裂和交往的中断,遮蔽了教育的交往性和伦理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活动,交往使自我摆脱了独白式的言说,[15]走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既使自我不再作为单子式的存在而不得不面对陌生化的世界,同时也不至于使自我陷入唯我论的危险境地。教育伦理生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方面它确保了教育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使自我成为走向他者的自我,摆脱生活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它能够以更高的旨趣驾驭单纯的学习生活和教育生活的内在必然性,使个体能够从片面的学习、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克服一切生物性对于自身生存的内在紧迫要求,不再使教育伦理生活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的束缚。倘若不能驾驭教育生活的必然性,教育伦理生活就变得不再可能。[16]68
二、被封闭的良知对教育伦理生活的逃避
市场经济在引发生活功利化的同时,也逐步使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子领域日益脱离政治的绝对权威,并摆脱传统的强制性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共识,走向道德的领域分化。道德分化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诸领域逐步从政治一体化转向领域分离,并赋予自身以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道德分化使个体获得了道德自主性,从而使“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17]25道德在现代社会的私人化使个体的道德信念和道德价值取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个体选择何种道德价值成为个人的私人事务,道德的终极价值在于个人的良知决断,传统的强制性、一元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得到了彻底的瓦解。毫无疑问,无论是道德的领域分化,还是道德的公私分离都必将极大的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和个人的全面解放。然而,教育自身的特殊性使教育领域的道德分化并未与社会领域的道德分化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教育自古以来便是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场所,政治信仰总是通过教育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传播。这也就注定,社会领域的道德分化不可能在教育领域完全实现,而只是有选择的对教育价值取向进行适当改造以使其适应当前的社会。如此以来,教育便不得不进行着双重面对,一方面政治的绝对权威依然存在,深刻的影响着教育领域的道德价值选择;另一方面道德的私人化已成为社会事实,学生与教师作为社会存在深受社会浸染。无论哪一方面都对当前教育伦理生活的方式选择发挥着决定性的制约力量。
政治信仰总是通过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或理性建构而成为普遍性的道德制约力量,它通过强制性的规范和灌输使自身成为真理的化身[18],并借助于道德教育和社会宣传而形成儿童以及民众对其真理性的信仰。真理性与普遍性使政治信仰摆脱现实生活的有限性而指向无限,它总是以“应当”的形式传递给受教育者关于美好未来的想象,并形成受教育者的价值期待和奋斗的动力。于是,教育中的道德至上就表现为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所谓的道德至上就表现为政治至上和信仰至上。[19]不过,政治信仰对普遍性的坚守使其难以关照现实教育生活的实然状况,它把自身当作一个绝对的普遍而直接通达未来,并通过“未来”、“人类”等遥远而抽象概念远离现实教育生活,形成对现实个人不可避免的压迫。如黑格尔所言,“这种思维死抱住普遍性,从而是非现实性的东西;它认识不到,如果概念要达到定在,概念本身就得进入规定性和特殊性,他也认识不到,只有这样,概念才能达到现实性和伦理客观性”。[20]于是,政治信仰就通过与特殊和有限划清界限而彻底的否定了伦理生活,它对伦理生活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因为它通过对无限的追求放弃了生活的现实性,同时也违背了真实的伦理生活。对伦理生活的逃避使道德教育成为缺乏现实性的空洞说教,道德永远封存于内心深处,遗忘了对他者声音的聆听,也放弃了对他者的责任担当[21],从而逃避了对现实的关照,在现实性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最虔诚的信徒身上我们往往发现了一颗冰冷的心”,“我爱人类,但却不能去用心爱一个人”的现实窘境。[22]
当然,政治信仰并不是道德教育的全部内容,学校道德教育同时体现在个体德性的教化。不过道德私人化的现实极大地冲淡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道德私人化一方面使个人走向道德自主,个体道德价值的最终选择取决于个体自我的良知决断,从而使个体的主体性得到无限提升;但在个体自主性得到确立的同时,道德的自我决断也诱发着教育内部道德共识的困境。传统的强制性的道德共识因为缺乏个体的道德自主性的参与,因而是并非出于自愿的共识,限制了受教育者自我道德能力的发展。但完全私人化的道德则引发公共道德的退场,因为道德价值的合法性的根源在于自我,任何超越自我的“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道德权威都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任何普遍性的道德规范都将被视为与个人自由相敌对而失去存在的空间。”[17]27,每个人都基于自我的立场而选择道德价值、道德规范以及终极的道德目标。于是,人与人之间道德价值、终极目的的冲突和无休止的分歧取代道德共识成为我们当下的首要面对,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共识反而成为不切实际的道德目标。于是,道德私人化在使绝对的道德权威退场的同时也通过对统一道德价值的消解而瓦解了公共教育生活所需要的起码的道德共识,教育伦理生活被寓于道德碎片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伦理生活如功利意识一样走向了道德的自我关注,尽管自我的道德良知依然存在,尽管受教育者依然会依据内心的道德法则对邪恶予以谴责、对善良予以赞美、对悲惨予以同情和怜悯,然而这些还不足以使自我超越私人的道德而将其转化为公共的道德行动。私德的泛滥降低了其对教育现实关照的有效性,从而是缺乏现实性的道德[23]。更为经常的状况是人们更倾向于将道德良知封存于内心。于是,我虽对世间悲惨的人们深表同情,但却对身边悲惨遭遇的人熟视无睹。毫无疑问,碎片化的道德与绝对的政治权威一样采取了对伦理生活逃避的态度。
三、自私的正当化与排他性的教育伦理生活
功利意识与道德分化成为时代伦理生活的写照,无论是功利意识还是道德分化都是与伦理生活相悖的,不能实现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精神,而精神的产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相互承认对方为具有自主性的独立意识,以及与他人在具有伦理规定性的共同生活中得以实现。功利意识与道德分化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教育生活的自我关注这一相同的结果,功利意识通过对必然性教育生活的彰显使个体将自我利益作为生活的首要目标,从而遮蔽伦理生活;道德分化则从两个极端将良知封存于内心,一方面政治信仰和绝对权威通过对无限的追寻使教育伦理生活失去现实根基,另一方面道德的私人化以及终极道德的自我决定使道德共识碎片化,丧失了对教育现实的规范功能。于是,教育伦理生活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的私人化道路,私人化意味着主体间交往的中断以及教育伦理关系的断裂,从而教育伦理生活最终走向了对伦理的偏离以至背叛,因为伦理表达的人们相互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离开了关系,也就无所谓伦理,伦理之为伦理就在于它总是超越自我以及自我利益而表达出对他者的尊重[24]。于是,教育伦理生活在必然性追求中放弃生活的伦理关照,在私人化的道路上遗失教育伦理生活的公共性。
教育生活是必然性生活和伦理生活的统一,必然性生活满足自然因果律的要求,伦理生活则满足自由律的要求。功利主义教育将教育过程简化为知识学习和知性能力养成的过程,从而使教育生活演化为因果律支配下必然性生活,必然性之为必然性在于它内在的决定于知识的逻辑和自然的秩序,而缺乏个体自由意志的参与。我们说功利意识遮蔽教育伦理生活就在于它通过自然因果律排斥自由意志,放弃在伦理生活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找生活的完善,而是在外在的必然性世界中寻求生活的救赎力量。必然性生活将伦理实体内的个体视为必然性世界中物化的中性存在,以中立的姿态认识和把握他者,无视他者的显现对自我之必然的伦理要求以及自我对他者之必然的伦理责任[25]。显然,对必然性的遵从以及无视他人的自私心态不断彰显并延续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26]尽管人与人之间依然在伦理实体中共存,但这种共存只是表现为必然性支配下的功利“需求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单纯的共在性”,[16]68只是一种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共关怀的孤立个体的麋集,真正的公共教育生活沦为没有公共福祉、公共目的的结构性共存,丧失了伦理实体所内在具有的相依、相存的伦理属性。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偶然,相反,它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支配下的必然性结果。这种内在必然性逻辑在其运行过程中逐步转化为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型塑出教育伦理生活虚假的公共性和绝对的自私性,从而使自私行为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合法性依据。功利意识所引发的这种人与人之间自私冷漠以及缺乏公共关怀的状况的根源在于生活在遵从必然性的同时失去了伦理的关照。完整的生活总是必然性生活与伦理生活的统一,对必然性生活的校正与补充也取决于生活中道德的力量。然而,道德的领域分化和公私分离的现实使其并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道德的私人化通过道德价值的多元化瓦解核心价值和道德共识,并将道德锁闭在内心深处成为自我关注的、不具有现实性的道德,进一步加剧着孤立化、冷漠化的教育伦理生活的现实状况。于是,道德的力量不但不能消解教育中自私行为的合理性基础,反而使自私获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并使人们“陷入到无节制的欲望追逐和自私自利之中”[27]。
自私的正当化使教育生活面对个体自私的膨胀缺乏公共道德的监控力量,个人利益和价值成为伦理生活的判据,从而不可避免的引发排他利益的生活格局。每个人基于个人理性对生活做出判断和选择,然而“个人理性的结果往往是集体的非理性”,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思维是单边主义的,由单边主义视野所规定的个人理性一心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28]90从而使教育生活不得不面对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个体依据个人理性寻求自我的有序生活,另一方面集体生活因个体缺乏公共的关怀和为他者考虑的意向而陷于排他性的无序格局。不过,这种悖论只能是一种临时的状况,而不具有持久的特征。原因在于在起点上,每个人基于个人理性安排自身的学习生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相安无事。然而,一旦这种基于个人理性的个人主义获得了隐性的制度安排并成为普遍化的力量,集体的非理性和无序将形成个人的理性生活秩序的终结。集体作为个体的生活空间,其无序状态不可避免的限制着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理性的发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人人追求排他性利益的最大化所导致的必然是人人利益受损的非预期性后果。而且,基于个人理性的生活是有“mind”无“heart”的生活,生活中只有“合理的”利益追求,而无“合情的人心交换”[28]91。显然,缺乏人心参与的个人生活因违背人性而难以持久的存在。最终,无论是个体生活还是集体生活都将走向无序的状态。
伦理是一种自发的生命表现,在原初意义上,伦理形成于自我为达成行动的成功所抱有的对他者的肯定性反应的坚定信念[29],以及自我对他者伦理要求的积极回应。因此,伦理既表达着他者对自我的伦理要求,也意味着自我对他者的伦理责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生活的基本事实,这种自发的相互依赖成就了自我“为他人考虑的倾向的可能性”。[30]302然而,它也只停留于这种可能性,生活中诸多的否定性力量随时可能打破这种可能性。教育伦理生活的私人化的直接后果便是个体用“为自己利益而行动代替了为他人利益而行动”,[30]302排他性的利益追求成为市场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基本人格特质。因此,教育生活的自我关注不可避免的阻碍了自我对他人伦理要求的实现,同时也自然的放弃了自我对他人的伦理责任。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伦理生活在排他性利益的追求中走向了去伦理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郭清香.伦理生活研究: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J].江海学刊,2006(3):64.
[2]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M]//梁治平.转型期的社会公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9.
[3]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69.
[4]高全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42.
[5]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9.
[6]黑格尔,G. 精神现象学:上 [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2.
[7]鲍曼,F. 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4.
[8]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78.
[9]艾略特,T.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04.
[10]斯特劳斯,L.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6.
[11]高兆明.“伦理秩序”辩[J].哲学研究,2006(6):108-109.
[12]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7.
[1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59-160.
[14]金生鈜.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09.
[15]泰勒,C.承认的政治[M]//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 董之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6]阿伦特,H.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 陈燕谷,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7]贺来. “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J].哲学研究,2001(5).
[18]姚本先,等.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高校教育管理,2007(5):58.
[19]张忠华.论传统道德方法论思想的现代价值[J].高校教育管理,2008(6):35.
[20]黑格尔,G.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16.
[21]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1.
[22]陈涯倩.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EB/OL].哲学论文.考试吧.(2004-12-13) [2011-10-11]. http://www.exam8.com/lunwen/zhexue/qita/200412/1395837.html.
[23]曼德维尔,B.蜜蜂的语言[M].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6-17.
[24]朗西埃,J.政治的边缘[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06.
[25]戴维斯,C.列维纳斯[M].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7.
[26]列维纳斯,E.从存在到存在者[M].吴惠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序言2.
[27]严从根,冯建军.美好生活和两种教诲——施特劳斯学派道德教育思想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1(2):57.
[28]赵汀阳.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J].哲学研究,2011(1).
[29]黑尔德,K.对伦理的现象学复原[G]// 倪梁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七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
[30]本特松,Y.实践的至善和伦理要求 [G]// 倪梁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七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张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