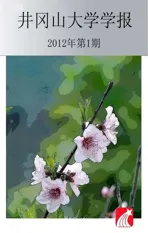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2012-04-18马艳辉
马艳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马艳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忠”、 “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 “忠”、 “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 “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 “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忠;孝;名教;门阀意识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对中国社会及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忠”、“孝”是史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司马迁《史记》“作三十世家”,记“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拂股肱之臣”[1](P3319)。班固《汉书》在对诸侯臣子的评价上,则以称赞贤能忠良之士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其命运并不过多与皇朝兴亡相联系,故而在有关“忠”、“孝”的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这不仅影响到当时史学的发展,也影响到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评论,即史论的发展。本文试就现存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忠孝问题上所发评论①目前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忠孝问题的研究论文,大致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直接以史论为研究对象,涉及到忠孝问题,如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宋志英:《晋代史论探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等。第二类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家、史书时,涉及到忠孝问题。如乔治忠:《孙盛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庞天佑《论范晔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第三类是直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观念,间接涉及到史论,如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见《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甄静:《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4期等。而直接以魏晋南北朝有关忠孝问题的史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则暂付阙如。,作初步比较、辨析,以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从中看出这一时期史家忠孝观念的转变。凡此,如有不妥之处,请学术界前辈与读者批评、指正。
一、“忠”的多元与淡化
“忠”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之一,其早期的内涵是很宽泛的,除了涉及到君臣关系,还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密切的关系。如孔子曾以“文,行,忠,信”[2](P73)来教导弟子,而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P39)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把“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从理论上把“忠”的内容变为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并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影响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长期得不到改变,君主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如西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3](P1315),揭穿了君臣之兴、礼乐之设,是用以统治民众的实质。东晋鲍敬言著《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慝日滋”[4](P509)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古者无君胜于今世”[4](P493),主张回到无君的古代。在这样的社会与思想环境下,魏晋南北朝史家一方面对“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重视,另一方面对“忠”的理解日趋多元,并对所谓“君臣之义”提出了质疑。
陈寿《三国志》对效忠前主而拒降被杀的臧洪评价颇高,称赞他“有雄气壮节”,而“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 ”[5](P237)而东晋史家徐众则认为臧洪“敦天下名义,救旧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义足以励薄俗”,但他“誓守穷城而无变通”的作法,却导致“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5](P236)。 南朝宋史家范晔也认为臧洪“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但其时曹操同袁绍刚刚结盟,而臧洪期望依靠袁绍,为张超解曹操之围,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也”,缺乏对客观形势的正确认识,不过依然是“力屈志扬”[6](P1892-1893)。 可见,徐众、范晔虽然对臧洪的具体作法有异议,不像陈寿那般予以赞扬,但都肯定其所为是符合“忠”的标准,虽然其效忠的对象实为“故主”非东汉皇帝。
东晋史家习凿齿在其所撰《汉晋春秋》中,亦极力提倡忠孝,凡忠于其君者,必称颂之。如曹魏大臣毌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代魏称帝,后以失败被诛。习凿齿身为晋臣,却评论说:“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君子谓毌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5](P786),称赞毌丘俭在曹魏危亡之时,竭尽臣节忘我赴义,是曹魏之忠臣。并由此高度评价敢于直言上谏的高堂隆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 ”[5](P717)他认为高堂隆敢于指出君主的过失,正是“忠且智”的表现。而对于屡谏不用、忿而拒命的张昭则批评道:“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懟之有”,认为张昭因谏言不被孙权所用,心生怨忿,在孙权“悔往之非而求昭”时,又“闭户拒命,坐待焚灭”[5](P1223),是有悖于为臣之道的。 北朝北齐史家魏收在《魏书》史论也多称颂北魏大臣之忠,如他以“忠以为心,盛衰不二,纯节所存,其意盖远”[7](P607)来称赞北魏大臣刘库仁兄弟。 而尉真兄弟“忠勇奋发,义以忘生”,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得以“增隆家业”[7](P660)。
以上这些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对“忠”的肯定和重视,也是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但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忠”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发展。如东晋史家孙盛将“君”与“臣”置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不是单一强调臣忠于君。他认为只有君臣皆遵守道义,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才能“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建立起牢固的统治秩序。因此他在评论三国时期袁绍的谋臣田丰、沮授时说:“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闇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丰知绍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规,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 ”[5](P201)可见,孙盛认为臣民不必单方面效忠于君,即“君贵审才,臣尚量主”。而田丰明知袁绍会失败,却“甘冒虎口以尽忠规”,是“虑不存己”的不智行为,应该“去乱邦,就有道”,明确反对其为袁绍尽忠的作法。
南朝刘宋史家范晔亦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提出修正。他在评论东汉末年的忠臣时说:“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6](P2120),对其持褒扬与赞赏的态度,却反对忠臣不知权衡利弊的过激行为,即“不识失身之义”。范晔对于“贤人”不知审时度势、一意孤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昔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6](P2211)他认为东汉末年张俭以一人之力弹劾中常侍侯览,虽然其“贤”为天下敬重,行事亦出于忠心,但由于不能审时度势,反而牵连多人,“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6](P2210)。
对于臣民如何对君主尽忠,范晔提出:“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6](P2094)。 他主张在“义重于生”的情况下,可去奋起舍生,而在“生重于义”、“上以残暗失君道”的情况下,臣下“全生可也”。这种认识与前代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臣对君的绝对忠诚相较,更强调从君臣两方面来看待“忠”,具有了更多辩证的色彩。当然,范晔虽然肯定“臣节”可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取舍,但他仍然对 “杀身以成仁”的忠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说明他对于“忠”的认识仍不出儒家之范围。与范晔同时代的史家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对于“忠”的理解却有不同于上述史家之处。魏明帝想营造许都和洛阳两城的宫殿,少府杨阜上疏劝谏道:“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裴松之针对此段疏文,发表评论:“臣松之以为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此则发愤为己,岂为国哉?斯言也,岂不伤谠烈之义,为一表之病乎! ”[5](P708)在这里,裴松之认为臣下不顾己身,甚至不顾性命也要劝谏弥补君主之失,才是“忠至之道”。而杨阜所谓“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称不上是为国尽忠。可见,裴松之所理解的“忠”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君主,而是为国家大利,为天下万民。
由此对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之事,裴松之赞赏说:“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5](P1022)他认为曹操有完成统一的能力和实力,假若孙权听从张昭的意见,则天下一统、免于战火。另外,从窦融、张鲁归降所受封赏的事实来看,他推断孙权归降后,仍可保其富贵。故而裴松之称赞张昭之谋略,是合乎忠的标准。综上可见,裴松之提倡“忠”不同于上述史家,并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忠,而是以天下、百姓利益为前提之忠。
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士族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所需要的一切,保家远比殉国重要的多。南朝梁史家沈约在其所撰《宋书》史论中提出:“出身事主,虽义在忘私,至于君亲两事,既无同济,为子为臣,各随其时可也”[8](P1904)。 他认为当“君”与“亲”,即“忠”与“孝”发生冲突时,“为子”还是“为臣”,完全由门阀士族自己选择,并不以忠节责人。不过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沈约还是要提倡“忠”。在对反对萧道成称帝的宋臣袁粲的评论中,沈约指出:“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认为提倡“忠贞”对于巩固封建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称赞“袁粲清标简贵”,“及其赴危亡,审存灭,岂所谓义重于生乎!虽不达天命,而其道有足怀者”,从君臣之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肯定。而其最终目的却是借赞扬袁粲,为梁武帝歌功颂德,即“昔王经被旌于晋世,粲等亦改葬于圣朝,盛代同符,美矣”[8](P2234)。 与他同时代的史家裴子野却认为“袁景倩,民望国华,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萧条散落,危而不扶”,“出万死而不辞,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 ”[9](P4208)裴子野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角度立论,要求袁粲有所作为,而赴死不过是“匹夫之节”,不值得大加赞赏。
其后,南朝梁史家萧子显在其所撰《南齐书》史论中,则对两世为刘宋皇室姻亲却背宋投齐,身至高位的褚渊作了辩护。他首先把褚渊与袁粲作了对比,提出“世之非责渊者众矣”。接着他指出魏晋以后“主位虽改,臣任如初”,“君臣之节,徒致虚名”。门阀士族在仕途上“贵任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其利益不受皇朝更迭影响,则“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萧子显认为褚渊是高门大族,“清涂已显,数年之间,不患无位”,是“有国常选”,因而没有必要为刘宋皇朝殉节。最后他甚至认为要臣子殉节,“责人以死”,是“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10](P439)。
南朝陈史家姚察在评论于萧齐代刘宋时拒绝把御玺交给齐高帝,但仍在齐、梁为官的谢朏时说:“谢朏之于宋代,盖忠义者欤?当齐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难,确然独善,其疏、蒋之流乎。洎高祖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 览终能善政,君子韪之。 ”[11](P266)他认为谢朏对于刘宋是忠臣,其虽在萧齐出仕,却独善其身,近于处士。到梁武帝时,才“首陟台司”,而这样“极出处之致矣”,都是正确的。在这里,姚察仅讨论谢朏个人与统治者的关系,忽视皇朝的更迭,这与沈约、萧子显之论,可谓异曲同工。
总的看来,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关于“忠”的评论上,受现实社会及门阀政治的影响,并不像汉儒极力倡导普遍的明确之“忠”,对于“忠”之观念日趋多元且淡化。
二、“孝”与名教的结合
相较“忠”的被漠视,同样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被门阀士族极力提倡,甚至形成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12]。由此门阀士族还进一步将“孝”与名教联系起来,即把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同自然结合起来,强调名分本于自然,为不可移易之准则,从理论上把“孝”提到了封建伦理规范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东晋史家袁宏在其所撰《后汉纪》史论中,对此作了充分阐述。他写道:“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称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13](P509)袁宏首先说明“君臣父子”是“名教之本”,即名教的核心乃是君臣父子关系。接着他又把君臣父子的关系同自然结合,赋予君臣父子关系以自然的属性。最后强调天地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成器”,即父子关系与仿效其而来的君臣关系也是不会改变的。可见袁宏认为父子关系是原始的、天生的,而君臣关系是后天发展而来的,把家族放在比皇朝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这种以父子关系为本的名教思想,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高道德规范。
与袁宏同时代的史家孙盛亦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史论中宣称“资父事君,忠孝道一”[5](P539),将“资父”放在“事君”之前。因此孙盛很重视为亲服丧,极力主张恢复儒家倡导的礼制。他针对魏文帝曹丕在服丧期间,“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於邑东”,评论道:“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义惇,臣子之恩笃,雍熙之化隆,经国之道固,圣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缞素夺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义感阙于群后,大化坠于君亲;虽心存贬约,虑在经纶,至于树德垂声,崇化变俗,固以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且武王载主而牧野不陈,晋襄墨缞而三帅为俘,应务济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 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5](P61)孙盛认为守孝三年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自汉文帝变更古制,就“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他激烈批评魏文帝服丧期间“设飨宴之乐”的行为,破坏了礼制是“坠王化之基”,“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并将曹魏国祚期短归根于此。他还针对曹魏时曹真、陈群、王朗等大臣以暑热劝止魏明帝为其父魏文帝送葬之事,批评说:“夫窀穸(墓穴)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群等之谏,弃孰甚焉! ”[5](P88)孙盛认为葬父之事,是“孝子之极痛也”,是人伦中最重要的事。更何况是魏文帝作为天子的葬礼,“敦礼者重之哉”,而魏明帝听从陈群等人的谏言是非常错误的。
南朝梁史家裴子野也主张坚守儒家倡导的为亲服丧的礼制,他针对刘宋大臣殷景仁在丧起职之事,评论说:“三年之丧,有生之巨痛,既贯天道,实惟民极。中世汙隆,或行或否,末世企勉,还尚典刑。而国之重臣,多从权制,因习渐染,遂以成俗。弃衰麻而服冕弁,匪金革而徇冦戎,君子辱乎上,小人通乎下,名教倒置,将安用之。茍非有为,已之可也。 ”[14](P315)裴子野认为在丧起职本是“国之重臣”不得已而为之,却渐成普遍现象,而这种作法将“名教倒置”,是应该制止的。裴子野还进一步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民之至德曰孝”,并阐述了他心目中圣人所制定的礼乐,即“朝夕安否,尝药侍膳,父子之礼也;陈诗齿族,纠合宴私,兄弟之乐也”。他认为这种礼乐若能贯彻,则“孝悌兴于国门,德教加于百姓”,“祸乱不作”[14](P318)。 此外,裴子野还作有《丧服传》之集注和《裴氏家传》之续写,以自觉发扬名教。
另一位南朝梁史家沈约在《宋书》的《郑鲜之传》中引其语宣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盖以类得之也”[8](P2212),并首创《孝义传》,记载了一批孝义人物的事迹。沈约认为“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8](P2214),而其撰述的目的就是要这种孝行“昭被图篆”,以有利于声教。他在表面上提出忠孝可并行,但在《宋书·颜延之传》却批评颜延之的儿子颜峻为宋世祖撰檄文,将其父置于危险的境地,是“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的作法,“以此为忠,无闻前诰”[8](P1904),并非是“忠”的表现。可见沈约实际上也认为孝是先于忠的,撇开忠而极力提倡孝,是其矛盾之处。他又进一步指出“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8](P2259),透露出门阀士族所提倡忠、孝的虚伪性。
南朝梁史家萧子显在其所撰《南齐书》中亦设《孝义传》,并引用孔子“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的话,认为“人之含孝禀义,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学至”[10](P955),并以父子关系为本,提出“孝为行首,义实因心”。这就是说,以父子关系为本的孝是高于君臣之义,明确将孝作为门阀士族的最高道德原则。萧子显称颂“色养尽力,行义致身,甘心垅亩,不求闻达”的行为,进一步指出在“浇风一起,人伦毁薄”时,提倡孝义,对于“扶奖名教,未为多也”[10](P967)。
与上述史家不同,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在对“孝”的认识上,则主要强调了“义养”的概念。他提出:“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6](P1293),认为孝敬赡养父母是孝道的根本,继承了前代儒家关于孝道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孝与不孝的区别在于不在于外在供养,而在于内心的真实情感,这是对前人观点的发展。范晔还进一步提出“大养”与“义养”的概念,认为若能修身养性报效国家,成就利国利民的大业,是最大的“孝行”;而通过正当途径去孝敬父母,比用不义之行去赡养父母更能体现孝心,是为“义养”。范晔反对为了孝道而行不义之事,认为是“孝之累也”。这是对东汉以来有关孝道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东汉末年借孝道盗取虚名,即“举孝廉,父别居”,这种名不副实现象的一种抨击。
北朝北齐史家魏收在其所撰《魏书》中也设有《孝感传》,他认为“孝”很重要,所谓“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却并没有完全将 “孝”同“忠”割裂或联系起来。魏收认为孝与不孝的区别在于孝养父母,即“始敦孝敬之方,终极哀思之道,厥亦多绪,其心一焉”,强调内心的真实感情,这才是真正的孝行。置于“负土成坟,致毁灭性”,他认为是“乖先王之典制”,不应提倡,主张“观过而知仁矣”[7](P1887)。 这同范晔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较之于其他南朝史家关于“孝”的评论,更为平实也更符合实际。
总之,魏晋南北朝史家关于“忠”、“孝”的评论,跟其所处社会、时代有关。东晋皇朝是在随之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支持下建立,进入南朝虽然庶族地主兴起,但门阀士族依然占据优势地位。而北魏鲜卑族拓跋部本是游牧民族,在同中原各族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封建化、门阀化,故北朝的门阀地主的势力不如南方强盛,门阀意识也不像南朝那样浓厚[1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史家关于“忠”、“孝”的讨论,其思想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但因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孝的地位逐渐超过了忠,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占据首要位置,成为门阀士族保家为先的理论依据。这正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情况,对于我们更全面认识这一时期史论的发展,尤其是儒家伦理观念在史学中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孔子.论语.[M].杨伯峻 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全三国文[M].严可均 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
[4]葛洪.抱朴子·外篇[M].杨照明 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54.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A].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3]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4]许嵩.建康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A].魏晋南北朝史研究[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On the Transition of Ideas about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n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 Yan-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China)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re two key concepts in Confucian ethnics.They not only make up a vital part in history compiling but also make a difference to appraise of historic figures.In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feudal lords and aristocrats took dominance of the society.Hence historian in that time,on the one hand,inherited but diluted the idea of “loyalty” in Han Dynasty,and on the other hand enthusiastically advocated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and established a doctrine that filial piety was the foremost ethical virtue.The ideas about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contained in those historian theories remained largely Confucian,but they reflected strong ideologies of feudal lord and aristocrats distinctive of that tim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loyalty;filial piety;Confucian ethics;ideologies of feudal lord and aristocrats
K03
A
10.3969 /j.issn.1674-8107.2012.01.019
1674-8107(2012)01-0114-06
2011-10-10
国家社科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时代特点与理论价值”(项目编号:09CZS001)。
马艳辉(1982-),女,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韩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