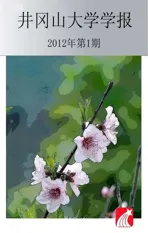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
2012-04-18王泉
王 泉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
王 泉
(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传达出多民族作家面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域所生发出的人生体验与生命的深沉思考。以王宗仁、凌仕江、王族、丁晓敏为代表的军旅作家的散文在追求崇高美中体现出英雄主义情结,祝勇散文在打破传统的体制散文中构建起了神性的空间,马丽华在纷繁的西藏文史故事中探寻着民间的意义,以平措扎西、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的散文则在民族文化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新世纪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代散文的创作。
散文;西藏;文化;崇高;家园
西藏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魅力是新世纪中国散文西藏书写的直接动力。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神奇的冈底斯山和纳木错湖,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尼洋河,组成了一幅幅醉人心脾的画卷。藏传佛教作为西藏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已根深蒂固。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等,无不受其影响,体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更是西藏魅力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以王宗仁、凌仕江、王族、丁晓敏为代表的军旅作家在军旅生涯中感悟着西藏的神奇,他们以军人特有的勇毅与果断,为世人描绘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祝勇在冥想中呈现出散文深远幽长的神性之美,马丽华则从西藏文史故事中演绎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而以平措扎西、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则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完成了对古老家园的回归及对新家园生活的憧憬。
一、军旅散文的崇高之美
康德认为:“崇高乃是‘纯然能够去思’之思能即足证明一心灵之能力可以超过每一感官之标准。 ”[1](P178)可见,崇高可以超越世俗的约束,让人达到人生的至境。军旅作家王宗仁认为:“思想代表散文的深度,散文之美,美于思想。我说思想,当然是崇高,是大美,是必须建立在作家丰厚的阅历与经验的基础上。 ”[2]他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被人称为:“用100多次穿越世界屋脊的记忆和40多年高原文学创作的沉淀,把青藏线和藏地士兵的表层生活叠加在一起,诗化为生命在极限状态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光辉。 ”[3](P48)王宗仁散文的西藏书写大都以真实的故事为依托,在夹叙夹议中表现了生命的顽强。
《雪山无雪》将20世纪60年代五个进藏女兵的故事与自己50年代末当汽车兵的经历串连起来,抒发了“风雪中孕育的故事不怕冻,越冻越新鲜的浪漫情怀。 ”[4](P5)《西藏驼路》写和平解放西藏时驼队给部队运粮之苦,死亡没有吓倒藏北无人区旷野上的驼铃声。“丁当,丁当!有时凝重,有时轻荡。凝重时正爬雪山,轻荡时跑在戈壁”。[4](P112)这是不屈生命的跋涉,更是西藏人民渴望新生的呼唤。《苦雪》是一出典型的关于军人与雪山誓言相守的寓言。不冻泉兵站代理站长宋珊在亲情与军人的职责之间毅然选择了坚守岗位。其儿子兵兵的不幸去世并没有打倒她,反而坚定了她扎根高原的信念。作家还有意穿插了文成公文进藏路上思乡心切滴泪成河的传说,从而将宋珊的故事进行了诗意的渲染。
《嫂镜》通过写美丽的军嫂雪莲在半个月里与士兵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表现了驻藏士兵对美的追求。而“一个在一些人看来也许很难下决心的棘手问题,排长夫妻就这么很默契地解决了: 雪莲给每个兵赠一张自己的彩照。 ”[4](P245)“彩照怎么保管,大家颇费了一番脑子,最后兵们商量出一个人人都拍手称好的办法:把她镶在每个兵随身带着的小镜子背面。兵们给镜子起名‘嫂镜’。这样,他们每次对镜整理军容风纪时都可以看到嫂子。嫂子也能看见她牵挂的战士。”[4](P246)军人的情怀与责任完美地契合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远山的雪路》通过自己突发性耳聋后与一位女医生的倾心交谈,传达出爱的哲思:“你爱生活,生活给你春风。你看朋友,朋友给你早晨。你爱女性,女性给你彩云。你爱自己,自己永远年轻。 ”[4](P306)作家回忆着自己创作《女兵墓》的情景,引发了女医生对已逝战友的追思。在藏北的谷露,女医生动情地写下了《阿妹的藏北》的诗。全文洋溢着感伤与怀想。
总的来看,王宗仁的军旅散文“通过描述人的生存,进而追寻人生存的意义,沉浸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在人的生命意蕴和高原军人与藏民族的交融中,既有今天的故事,又有往昔的故事,将历史记忆、故事传说与现实情景相互沟通,在今与昔的对接、渗透与徘徊中,令人感到一种生命的沧桑与反思,从而使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厚与深沉。 ”[5](P256)而这正是一种化悲为美的艺术努力。
凌仕江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二十年的雪域生活体验铸就了其散文飘逸、空灵之美。在他的散文集 《西藏的天有多蓝》、《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西藏的天堂时光》中,“他用十二年的青春和西藏对话,这种对话是和圣山圣水,是和神的对话。 ”[6](P5)作为一名诗人,凌仕江自觉地将诗的气韵融合到散文创作中,在丰沛的意象中构筑起行云流水般的韵致。“蓝天”意象在其成名作《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中凝固成永恒的美。“天天,天蓝,白天黑夜地‘蓝’着地球之巅的人们。有一回,一朵巨大的乌云忽然飞过来,久久凝固在布达拉宫的上空,大鹰的翅膀撞击乌云的一瞬,布达拉宫呈现红白分明。 ”[7](P42)以动写静,显示出蓝天特有的宁静。凌仕江善于从细微处入手,发掘生活本身给予人的启示,并借自然之美反思现代文明。
“风过无痕,天天天蓝。鹰不飞,天感觉干净。狗不吠,天蓝得发空。天天天蓝,与谁都无关,天天天蓝,谁都有关。人与天永远隔开着,像愈合不了的伤口。人在天下看天,天在天上看人,看人在天底下的一场烟火表演。天,把人看得很矮——同在一片蓝天下,人比人高不了多少。但天和蓝又习惯包容万千纷纭愁和欢。 ”[7](P43)这里写出了天的广阔胸怀及人对自然的依赖,从而升华出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
《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以回溯的话语方式反思都市空间。作家在追忆边城错那的军旅生活中触摸着西藏人的精神。“云朵是西藏人灵魂的知己,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我蹚过冰河想去发现一种牛粪精神,可我发现的只有云朵。平生最爱西藏的蓝天,走出那片天之后,我才发现城里天空的蓝,都是假的,只有点缀在西藏最西边的那些云朵真诚得让我梦里放歌——”[8](P231)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曾经的青春激情岁月是梦中最美的歌。如果说徐志摩在剑桥所遭遇的刻苦铭心的爱情让他终生不悔的话,那么,凌仕江在西藏的边境小镇与藏族人民的鱼水深情已化作云朵的真诚,在心里生根发芽。
《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书写了“自己身在城市,心却总在西藏”[8](P237)的孤独。 《我看见珠峰在移动》通过一个梦来表现了哨兵的寂寞,整篇散文充满了诡异的想象。“夜里我做梦,云卷云舒的珠峰是妩媚的女神,云开日出的珠峰脚下的大风中匍匐前进,珠峰突然向我移了过来,压倒了哨所,我听见世界一声巨响,腾空而起的我跳进了特堤斯海,冰凉的水花打在我的脸庞,随着一声尖叫,我一下子从床板上弹了起来,窗外蓝蓝的天正看着我不说话。 ”[8](P250)这里显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将军人为保卫国家安全守边防的浪漫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雪”也是西藏常见的自然景物,在作家眼中,它更是当地的神秘文化的一个缩影。他将视角从自然之雪转向了跟在藏族老人身后的一群羊,通过一只怀孕的母羊被汽车压伤后几个男孩救羊的情景描写,形象地刻画了藏族人对羊崇拜的心理。而“我”则看在眼里,默念着故乡。从“雪”到“羊”,作家抒发了关于西藏自然地域与人文风情的心灵感悟。雪落无声,正是作家想要传达的一种走进西藏的方式。
《西藏的天堂时光》和《说好一起去西藏》中的散文更多的凝聚了人文西藏的底蕴,从中生发出关于生存与生命的思辨。他在《面朝西藏,格桑花开》里打开了通向西藏的心径:“其实,西藏仅仅只是一条路,很多人走在通往西藏的路上。我不知道走向它能否走向天堂,我只知道通往天堂的路并不好走。从拉萨的任何一个方向出发,你都不能奢望一路有树,但只要你面朝西藏,就能看见格桑花开。这就是我对西藏现在进行时的表达。”[9](P5)《在高原上坐下来听风》赋予风以宗教的美:“在西藏,风中的眼睛常常看见绛红的光被风撕成碎片,满高原的飘啊飘,飘到牧女脸上就成了灿烂的高原红,飘到男人身上就成了青铜的骑手,飘到扎西次日山上的嘛嘛身上,那眯缝着的双眼就可以看见神殿里静坐的一排又一排的小小的佛。漂泊与失落忽冷忽热,记忆与忘却忽远忽近,苍凉的生命在风中被久久延续。风传递着情感与精神,风托起净化的心灵,撒给大地——沉郁、哀伤、悠长、崇高。 ”[9](P103)在这里,作家借风写出了藏族人特有的健美与皈依佛教中的坚韧精神,达到了具象与抽象的完美统一。《内心的河流》写历史积淀丰厚的拉萨河,将它的传说与诗人高洪波、李小雨、舒婷、林莽赋予它的想象及桥上哨兵的严厉进行了片断似的连缀,给人以沧桑之感。《西藏之北》恰似一篇充满悲情的童话。在大雪茫茫的藏北,牛羊被冻死,少年朵朵与羊羔奄奄一息,英武的解放军女护士出现了,她看见了比自己更坚强的朵朵。感人的画面与悲怆的故事相交织,象征着生命不息中的军民深情。
《三个美丽的解释》、《我和黑颈鹤有个约会》都是写藏族少年的感人故事。前者写卖土特产的林芝少女的聪慧善良,后者写安多县的小卓玛保护受伤的黑颈鹤的那份执着。都展现了藏族人民的厚道与真诚的人性美。另外一篇《雪山的声音》类似于复调小说的结构,书写了少女琼玛与雪山及爷爷的对话,以少女的纯真反衬出盗猎者的残暴及对现实生活的无情摧毁。
他的最新力作《喜马拉雅组曲》抒发的是“人不仅要亲近自然,还应和自然持有距离”[10](P127)的思绪。《拜水》从藏族人对水神的崇拜中感悟到生命的可贵。“对于拜水这样的仪式,在藏区观望不如想象,想象很可能导致你在疲倦的旅途中停下来,一不小心就带着失望的心情上路了。那里,你的思绪还在水中漫游,而我的回忆只会在河中驻足,因为我正在一点点地融入。 ”[10](P126)“融入”更多的体现了作家关于藏族人 “对水再生功能的痴迷和对天体星云的信仰”[11](P134)的理解。 《屋脊的屋脊》从藏族人对牦牛的崇拜升华出哲思:“让牦牛头颅回到玛尼堆上去,让自己的心灵回到自然的伤感中去,让真正的牦牛居住在圣洁的屋脊。佛在因此微笑,他在风的掌中露出了一排排雪白的牙……”[10](P132)《无名湖无名鱼》 让读者从边防连关于“无名鱼”的故事中看到了军旅生活知足常乐的民间境界。《太阳,向西向晚》抒写了尼洋河偏西村庄的老人坐在经石上守望心灵纯净的那份可贵。面对河对岸现代文明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的衰落,老人很无奈,“我”也感到茫然:“我停在他的背影里,犹如停在异乡,看见霜降似大雪。村庄在隐没。我抱也抱不起,我抱也抱不动,他的村庄比我重。我心上的故乡,我的湖水,我断裂的世界……不知他明天是否会在太阳升起以前远望小镇过尼洋。 ”[10](P136)藏汉两代人的茫然不尽相同,前者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后者则以“他者”身份审视着藏传佛教文化的魅力,继而返观自身,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迷惑与不安。
“西藏蕴含着无数的神奇,而凌仕江以年轻而善感的心发现和体验着西藏自然中的神奇。在这样一个被科学和理想所阐释的现代社会里,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写实与神话自然转换的叙述空间。当然,他的神话不是宏大叙事意义上的,而是细腻的,由意象和细节呈现出的神性。 ”[12](P50)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他对西藏高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全身心投入,才产生了让人心醉的审美效果:身处自然,心向宇宙,于幽远高阔的视野里折射出无我之境。
王族的军旅散文集《兽部落》中的一些作品用内心的生命激情与人文理性打通了人与自然的阻隔,让西藏的动物乐园成为人类心驰神往的一片净土。他的散文体现了维科所谓的“以己度物”的认识自然方式,“它把人同自然物在形态上、物质上、生命现象上加以类比,并以人的心理去领悟和解释自然物的活动,自然物的生命现象。把自然对象都视为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和相同的情感活动的东西,在对对象的观照、比较中呈现出生命的情感交流现象,从而产生与自然物的‘同情共鸣’和物我交融的同一境界。 ”[13](P155-156)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错觉: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才是美的使者,动物只是在适者生存中保持着其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王族以西藏特有的生命物种为描述对象,在亲身体验中,发掘出了动物的“自在”之美,即它们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所散发出来的自然生命之美,呈现出生态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兽部落》中,王族从牦牛、雪鸡、鹰等动物身上探询着动物的家园意识及对人类的启迪。牦牛“在一个地方吃草时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从不践踏草木,不从不随地大小便。受牦牛的影响,许多动物都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但至今很少有人知道牦牛的这一美德,更不能对动物中的环保形象大使给予准确的定论。 ”[14](P61)而人似乎在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制约下,在后工业文明的影响下,商品化意识日益膨胀,而家园意识则渐渐远去。牦牛的这种可贵的品质,正是当前人类社会急需的。雪鸡作为雪域高原独特的鸟类,在王族看来,它的壮烈之美来自于它的舞蹈。“就像是一位从容不迫走向刑场的少女”。[14](246)羌塘草原的人们也因为它产生了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养雪鸡的女人,不被人理解,从反面映证了它的纯洁与高雅。
鹰在人们的想象中是一种凶狠的鸟,是力的象征。在王族看来,“人不可能接近鹰,鹰对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依靠。”在西藏阿里,鹰对人亲近的故事及小鹰成长的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作家还根据亲眼所见,对一些关于“鹰群”[14](P191)的臆想提出质疑,还给读者以真相。
于晓敏作为一名女性,她的军旅散文以清澈细腻的叙述见长,多表现西藏日常生活的情趣,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灵感的迸发,只是西藏的美、诗意的、神奇的瞬间。所以我在我的关于西藏的叙述里,总是看到一些非理性的成份,那种跟理性若即若离的主观的感念,那种称为情感的东西,这种情愫跳荡在我的情绪里,指使着我的笔,于是,字里行间就摇曳着夸赞的味道。 ”[15](P52)《你的生命长成了传说》追忆士兵彭洪奎为按时归队,在大雪覆盖的高原上步行100多公里终因体力不支而倒下的悲壮之举。作家一边叙述各种传说,一边感叹:“你的纯粹高于生命。从此,你永生了,你的生命携着你无边无沿的传说,在无记忆的雪上坚硬地生长。 ”[16](P64)悲怆之情油然而生。
《寻找杜鹃》写原始森林里的杜鹃卓然不群的品质:“她用她的花香引诱着红松树浆,透析出一种非树非花的特殊味道;她的头紧贴着雾状树挂的边梢,随微风中轻摇的树挂一起摆出织锦的样子。她和森林里抢眼的金黄色迎春花以及亮丽的红柳遥相呼应。她横扫了所有小树的面子,使它们抬不起头,仿佛只要她在就须永远矮着,她在再度飞扬的生命流程里迅速长成了一棵树。她使这森林里的植物高的是高,矮的是矮,这森林因她的存在就别样地纯纯粹粹了。 ”[17](P64-65)而热爱杜鹃的英俊文书却扑倒在杜鹃树下,以生命同杜鹃进行了一次完整的碰撞。悲得令人心碎,美得妙不可言,这便是对生命价值的顿悟,“真朴中包含着浓厚情意,平淡中寓存着绚烂之性灵,谐和中充盈着蓬勃之美。”[18](P55)《西藏叙述》通过写西藏人弹酒、拍女性臀部的手势,西藏的语言和多姿的语境,表现了民间生活的情趣。《蝴蝶的日子与故事》叙述了土纸和食物尼楠的由来,娓娓道来,飘逸出平和、冲淡的审美追求。可见,于晓敏散文对细节的把握,使其散文在以小见大中将情感之真和盘托出,获得了审美张力。
另一位军旅女作家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以采访的经历,真实记录了在西藏默默无闻奉献的人物,有军人,也有作家及科技工作者。《青山埋忠骨》写边防团长高明诚带领小分队为勘察边界而牺牲的故事,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爱西藏的男人》写了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及90年代三代军人对西藏的爱。“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19](P20)这是军人职责的写照。 作家写军嫂,把她们比作“高原温泉”,突出了她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的感动。《爱西藏的女人》则写了为发展西藏的太阳能事业只身去藏的“张太阳”,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及作家马丽华的风采,从一个侧面书写了女性对发展西藏作出的贡献。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克服危及生命的高原反应,忍受寒冷与寂寞。作家还写了高原特有的杜鹃、柳树、苹果树非凡的品质。她以杜鹃喻雪山上的士兵,极言驻藏士兵的高洁;她写西藏的柳树和苹果树,追溯到50年代十八军种树的艰辛,让人不禁为开拓者的精神由衷感叹。
“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人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所以对我来说,每次去高原,都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与老朋友的会晤和交谈。 ”[19](P2)裘山山正是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在与人的灵魂对话中,让我们感到了弥足珍贵的心灵纯净。
整体而言,新世纪军旅散文的西藏书写在极限体验中表现了高原生命的顽强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军人的人格魅力,这正是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英雄主义情结的体现。无论是男作家壮怀激烈的感言,抑或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还是女性作家行云流水般的倾述,都凸现出化悲为美的艺术努力,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二、祝勇散文中的“哲学高原”与马丽华散文的文史传奇
在祝勇看来,“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 ”[20]他的文化随笔《西藏,远方的上方》在行走西藏的大地中思考,在思考中将读者带入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纵深视域,是一种典型的思辨型散文,“即重思考,缘事缘物寓理,作者以现代意识为烛照,跨越时空,对祖国、民族、历史、现实、命运、伦理、献身的热忱等进行深入的思考。作者站在时代前行的角度,以哲人的头脑对社会、自然、历史、人生的改变与发展提出‘警世’与‘超前’的意见,充满了开放意识、民主意识、人道意识与科学意识,因而对于人性的完善和健美情操的陶冶和培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1](P134)作为“新散文”的代表作家,祝勇主张“使散文回到自身”[22](P41)他以身体的行走把西藏的想象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隐喻空间。
祝勇对西藏的动物情有独钟,总会发现它们与众不同的精神。羌塘的鹰是“人类头上的一个精灵”,“它们的姿态犹如藏文字母一样飘逸舒展、伸缩自如,它们共同拼写成往返于人间与天堂的神秘经文,它们是对天地间这幅无比巨大的唐卡最具深意的注释。 ”[23](P14-15)借鹰写风俗,可谓神来之笔。他从草原狼的柔弱里读懂了其“孤独和忧伤”,又从牦牛成为牧民的精神图腾中看到了自然赋予人类的神奇力量。而面对天葬这种习俗,祝勇从科学和神学的角度予以辨析,读懂了藏民生命意识的独特性。
关于西藏的历史与传说,祝勇也游刃有余地自由出入其中。“在祝勇的取景框里,历史不仅是时间的存在,更是空间的存在,它立体、多面、富于层次。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历史,就会有不同的细节呈现,虽然这些细节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能让我们在惯常的描摹中看到别样的风景。 ”[22](P43)他从布达拉宫的历史沧桑中看到了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布达拉宫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墓碑,“空间以它的最高形式进入时间,在它们的交叉点上出现的是墓碑。通过把时间凝固在空间中,墓碑表露了生命对时间和空间有限性的抵抗。 ”[23](P71)这实际上把布达拉宫置于历史性与共时性的阅读空间,给读者以陌生的一击。他从仓央嘉措的故事里悟到的则是爱情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也是一种宗教,它并非世俗生活的附庸,而是有着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逻辑体系。 ”[23](P131)仓央嘉措作为一位民间英雄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祝勇散文的西藏书写不同于一般旅行者的心情散记,而是力图穿越历史的尘埃,构筑着感性与知性的话语空间,充满了思想的穿透力。阅读祝勇如同与一位智慧的哲人倾心交谈,不知不觉中就会沉醉于他所描绘的神性世界,即他的西藏书写自觉地将哲学之思与西藏文化的神秘性融合在一起,让人获得了人生的顿悟。
与祝勇散文把历史只作为一个背景,强调从中引发的哲思不同,马丽华的《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在试图复原历史原貌的努力中探寻着藏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她从历史的富矿中,开掘和撷取了永恒的情感和精神营养,还原了一个时空清晰的高原演绎史,给人以新的感动与心灵震撼。 ”[24](P131)
“民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一是作为价值立场的民间价值取向,也就是自觉地把‘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在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中发现精神寄存的意义。 ”[25](P214)马丽华以其丰富的阅历与精妙的思考,重新发现了民间的意义。即她从大众心理和读者需要出发,发现了藏史中的传奇部分,寄予了一名作家兼学者特有的文化关怀。
《马和犬怎样成为人类朋友》从藏族动物神话中忧思着马在日常生活中的退场。《澜仓江畔的上古村庄》从卡若林村庄的制陶工艺中发现了端倪:“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西藏文化,一端连接西南山地原始文化,一端连接黄河旱作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共生共荣。 ”[26](P32)《外部世界有关西藏的传说》从昆仑神话的主神西王母的传说中探究着中华多民族共同的源头。《吐蕃的遗产,敦煌的缘分》从吐蕃人的宽容中感叹着藏汉文化交往的弥足珍贵。《古道上的白色运茶神》从咱塘村运茶神的传说中联想到茶马古道形成的“以茶易马,汉藏一家”[26](P250)的佳话。
与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相比,马丽华新世纪的作品不再是借旅行经历还原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西藏,而是执著于西藏文史故事,但不拘泥于成说,而是着眼于民间故事里衍生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为读者重新发现西藏历史,反思现实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从行走到反思,马丽华的西藏书写完成了又一次祛魅过程。
三、平措扎西、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散文的家园意识
家园作为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故乡,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家往往在时空的追索中产生了难以释怀的文化情结。在新世纪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中,藏族作家平措扎西的《世俗西藏》、扎西达娃的《古海蓝经幡》及丹增的散文《生日与哈达》的家园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平措扎西的笔下,西藏的历史、民风、民俗是一种流动的人的世俗生活。黄房子中的“堂木钦”神、藏历新年中的“顿钦”仪式都与布达拉宫的神圣相互依存。《往日灯火》写藏族人家中常见的长明不灭的酥油灯,也充满了神圣的色彩,它有十项作用:“世间变为火把,使火的慧光永不受阻,肉眼变得极为清亮,懂得善与非善之法,排除障视和愚昧之黑暗,获得智慧之心,使得在世间永不迷茫于黑暗,转生高界,迅速全面脱离悲悯。 ”[27](P124)这将藏传佛教的生死观表现出来。《藏历新年说羊》将藏族羊文化的魅力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绵羊和山羊是同出一辙的畜牧,但藏族人偏爱绵羊,新年的供品上只摆绵羊头不摆山羊头,放生羊一般只养绵羊,偏爱吃绵羊,把牧羊人称作绵羊人,甚至绵羊和山羊同样向人类提供粪料,让人烧做肥料,可人们在生活中只说绵羊的粪,正如藏谚所道:山羊的粪,绵羊的功劳。 ”[27](P152)《充满灵性的马》写马文化在西藏的演变。从对过去人们对马的崇拜到现代社会马的家园的消失,表现出对西藏马文化的独特领悟。神马、骡马、旅游用的马,马的商业功能被强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马的原始的生命力沦丧的悲哀。《藏乡酒话》和《藏乡茶话》写出了藏族人对酒和茶的偏爱:“在西藏,酒是人们快乐的相伴,也是人们痛苦时的相伴。 ”[27](P87)而酒歌、茶经又成为藏族文化中的亮点。
在长篇散文《古海蓝经幡》里,扎西达娃以小说家的智慧向我们展示了自己耳闻目睹西藏今昔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对西藏文化的留恋。《初见布达拉》、《古堡的覆灭》、《老城区》等散文既有儿时进藏时关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的零星记忆,也有对日喀则老城区幽静中神秘女子的臆想,道出了特殊年代人性的光辉。《逛新城》在感叹80年代拉萨的变化的同时,返观昔日繁华的市场、香烟缭绕的大昭寺和夏天林卡的逍遥。《沐浴节》写现代文明对沐浴文化的侵入,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扎西达娃笔下的一些人物,如孤独的扎西、美丽的珞巴族舞蹈艺术家亚依、背水的藏族姑娘和驮盐人格桑,几乎都是西藏文化的象征。扎西对佛教的执着追求,亚依从放牛娃到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乃至梦想当作家的渴望,将陌生的内地文化人抱上马背的背水女人,格桑对驮盐即将消失的沮丧,都在昭示着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
另一位藏族作家丹增的《生日与哈达》则通过80年时间沉淀下的感情记忆写了自己在童年过生日,在“文革”期间的狂热及在莫斯科自己给自己挂上哈达的三个情景,抒发了对母亲的深情。五岁的生日过得繁杂而漫长,给作家留下了挥不去的记忆,尤其是向莲花生大师的法像磕头的宗教仪式及向占堆活佛磕头的情景,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我给占堆活佛磕了16个响头,意味着16个圆满的佛缘,也希望老师将16部佛经传承给我,更标志着我已经把老师视为自己的又一个父亲。 ”[28](P82)而母亲给“我”的祝福更是令“我”惊讶:“她躬身向我献上了一条哈达,然后跪在地板上,工工整整地向我磕了三个头”。[28](P84)在童年视角中写出了宗教仪式的神圣。后来在西藏,母亲到拉萨来讲述了那条“阿西哈达”的故事,原来那是奶奶留下来的象征着仁慈、友爱的传家宝。再后来“我”回家看望年迈失明的母亲,又把那条哈达献给母亲。这条哈达所传达出的母子深情跃然纸上。“当这条珍贵的哈达在我5岁那年挂在脖子上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期望,当它在我22岁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心要过一个‘革命化的生日’,而忘记了母亲的苦心,当我在莫斯科自己给自己挂上这条哈达的时候,我只能怀念母亲的温暖,感恩母亲的慈爱。现在,这条连接着我们母子一生的温暖、思念、牵挂、祝福的哈达,一端告慰母亲的灵魂,一端紧系着我深深的怀念。 ”[28](P99)内疚、忏悔与思念交织在一起,凝聚了强烈的家园诉求。
“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双重压力让藏族女性失却了女性的娇柔,双重的艰难锻打出雪域的女儿的‘刚性’,使得她们不得不独立承担起生活施加给她们的重负。 ”[29](P127)格央、吉普·次旦央珍等新生代女作家的散文则深入到藏族女性的情感生活中,通过女性意识的呈现,表现了对新家园生活的憧憬。格央的《雪域的女儿》对藏族起源神话中“忠厚的猕猴与狡诈的女妖”的大胆质疑,实际上是对西藏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受到歧视的不满。相比之下,吉普·次旦央珍的《笑忘拉萨》有更多的自传色彩。她有时从历史的背影中思索沧桑巨变中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有时则以女性个人与男人的情感来探讨藏族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帕拉——风吹梦不停》从作为西藏贵族的奶奶阿旺白姆锋芒毕露桀骜不驯的个性中,看到了时代风雨中女性成长的轨迹。《长者》写姨夫从小到大对自己的关心,《至爱无言》写父爱,通过书写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男性形象,折射出人间真情对于女性成长不可或缺的意义。
藏族作家 “意识到在多元文化充分交流的情况下建立本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不拒绝吸纳先进民族的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的文学依附于他民族文学而存在,仅仅成为他民族文学的一种附庸物。他们要以肯定自我而绝不是否定自我的方式,理直气壮地进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兼容并存的大格局。”[30](P5)他们西藏的书写不同于非藏族作家对西藏神秘感的体悟和浪漫风格,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对本民族心灵故乡的探求,有着特别的意义。
四、结语
西藏通过新世纪中国散文作家主体的想象和创造,获得了诗性空间,传达出多民族散文作家面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域所生发出的人生体验与生命的深沉思考。军旅散文在追求崇高美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情结,祝勇散文在打破传统的体制散文中构建起神性空间,马丽华的散文在纷繁的西藏文史故事中对民间意义的探寻,藏族作家的散文在民族文化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都是追求神秘感、浪漫风格和淳朴民魂的西藏文化精神的体现。这为我们解读西藏书写中的人生追求与人性美提供了坐标。新世纪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代散文的创作。
[1][德]康德.判断力之批判[M].牟宗三 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宗仁.散文美于思想[N].光明日报,2010-06-11.
[3]丁晓平.藏地密码的钥匙——读王宗仁散文集《藏地兵书》手记[J].军营文化天地,2008(12).
[4]王宗仁.藏地兵书[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
[5]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6]郭小东.许多人的故乡——序凌仕江《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7]凌仕江.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J].中华散文,2002(6).
[8]凌仕江.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9]凌仕江.西藏的天堂时光[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7.
[10]凌仕江.喜马拉雅组曲[J].十月,2010(3).
[11]林继富.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王雪瑛.就像格桑花在阳光下盛开——读凌仕江的西藏随笔[J].西藏文学,2009(2).
[13]邱紫华.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4]王族.兽部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15]于晓敏.是什么在牵引着我[J].西藏文学,2008(5).
[16]于晓敏.你的生命长成了传说[J].西藏文学,2002(2).
[17]于晓敏.寻找杜鹃[J].西藏文学,2002(2).
[18]徐琴.于晓敏散文创作漫谈[J].西藏文学,2008(5).
[19]裘山山.遥远的天堂[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20]祝勇.西藏,远方的上方·自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21]傅德岷.新世纪散文的跨越与发展[J],求索,2002(4).
[22]郭冰茹.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J].文艺争鸣,2008(4).
[23]祝勇.西藏,远方的上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24]宋美华.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评马丽华《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J].当代文坛,2010(2).
[25]王光东.民间[A].冯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6]马丽华.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27]平措扎西.世俗西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8]丹增.生日与哈达[J].十月,2009(3).
[29]普布昌居.试论《雪域的女儿》对藏族女性生存境遇的审视和思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30]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Portraits of Tibet in Chinese Essays:First Decade in the New Century
WANG Quan
(Scholl of Literature,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China)
The portraits of Tibet in Chinese essays in the 2000s reveal the reflections of writer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on the living experiences and lives through their scope of Tibetan history,culture,nationality and fields.The army-group essayists,typically Wang Zongren,Ling Shijiang,Wang Zu and Ding Xiaomin,pursue heroism in the loftiness;Zhu Yong constructs a universe of divinity by breaking traditional intra-system essays;Ma Lihua searches the folk significances in the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Tibetan literature stories;and the Tibetan-native essayists like Puncog Tashi and Tashi Dawa imply strong awareness of home in their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The portraits of Tibet in this era add something to the flourish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ssays.
essay;Tibet;culture;loftiness;home
I207.6
A
10.3969 /j.issn.1674-8107.2012.01.013
1674-8107(2012)01-0075-08
2011-10-08
国家社科
“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项目编号:09BZW059)。
王 泉(1967-),男,湖北洪湖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刘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