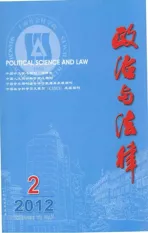“农民工”身份问题的法律分析
2012-01-28温晋锋郑立俊
温晋锋 郑立俊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南京211816;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检察院,安徽滁州239000)
一、“农民工”身份定位的困局
“农民工”1这个称谓由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2当时是指代“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的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总称。但在提到这个词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它的隐性评价意义。隐性评价意义是指人们对所指对象的委婉含蓄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所指对象的非本质属性的主观认识。3这种隐性评价是社会对这类群体地位卑微的自然反应,来自于深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从而导致在名称称谓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现代汉语词典》将身份解释为“人在社会上与法律上的地位”。4身份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基础,但“农民工”包含了多种身份属性。
“农民工”从字面上来看包含着两个词:“农民”和“工人”。“农民”在我国是一个多位一体的复杂概念,它可以是一种职业、一个阶级,更多地也是一种身份符号。5“工人”是一个职业概念。“农民工”一年中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镇中从事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他们属于广大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却又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类群体。“农民工具有的身份属性使其与农民一样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和静态的规定,而其他的职业是人们获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6
河南青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表面上是他的具体权益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保护,实质上是“农民工”身份定位的摇摆造成的。我们可以将“农民工”理解为农民或是工人,也可认为“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城市在经济层面上接纳进城务工农民的同时,在社会身份的层面上排斥这一群体,除了每年一度的春运和讨薪时人们会想起“农民工”,其他时候他们常常被社会所遗忘。
二、“农民工”身份固化的表现
称谓,指人们因为婚姻和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建立起来的名称。“农民工”这个称谓的出现显然是由身份和职业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是这两种属性使“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固定下来,并得到广泛运用。
(一)“农民工”称谓固化的政策表现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每年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关注了“农民工”群体,并提出了许多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其中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年3月国务院在严控新设办事机构的要求下,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特别批示,加设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专门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二)“农民工”称谓固化的法律表现
虽然国家对“农民工”的规定,并没有上升到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高度,但其出现于某些规范性文件中,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具有法的一般属性。在国务院的许多规范性文件中就规定了“农民工”概念,如2003年9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及2006年3月31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地方政府的法律文件中关于“农民工”的规定多如牛毛。有些地方的权力机关甚至准备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以此将“农民工”彻底固化为一种特定的法律主体予以规范。
(三)“农民工”称谓固化的舆论表现
社会舆论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某一事件或某一群体有效的公共意见。张友渔认为“舆论是把少数人排除在外的社会多数人的意见。”7社会舆论对外来进城人员的主观恶意猜测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科亨就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人们一般都采用移民中少部分人最为消极的特性——犯罪、占用大量福利、素质低下来涵盖其他的移民,8认为这类人群中的成员都是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二等公民”。其实“农民工”这个称谓并非是进城务工农民用来自我称呼的,而是新闻媒体、城市居民对于这一群体的称呼,体现着社会舆论对“农民工”群体进城后衍生的负面影响的感受。
(四)“农民工”称谓固化的学术表现
社会热点一般都是学术界所研究的对象,“农民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学术问题,学者们以“农民工”为对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农民工”身份认同、“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就业、“农民工”权利救济、“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自身的个体差异、“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等等。这些学者都从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农民工”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逻辑起点进行“农民工”具体权益保护以及代际差异的理论研究,从而使得“农民工”这个概念在学术上日渐固定化,并影响到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导向。
三、“农民工”概念的法律质疑
(一)“农民工”概念的词义分析质疑
“农民工”作为一个日用语,不仅仅是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称呼,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带有社会公众的主观印迹。一般词语所蕴含的主观态度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有失偏颇的。而包含着偏见和歧视的词语在社会舆论和规范性文件中广泛使用是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在国外的媒体组织中,如美联社对其新闻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少用俚语,因为许多俚语如“胖子”、“黑鬼”等都带有歧视意味。但在我国的社会习惯用语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有不少“农民工”这样的概念。虽然与“农民工”具有相同意义的称谓“打工仔”“打工妹”也很盛行,但是“打工仔”、“打工妹”只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农民工”概念却体现了国家和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贬损。一个歧视性词语的通用,显示出了这个社会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默认甚至纵容,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坚决抛弃如此使用歧视性词语的作法。
(二)“农民工”概念的规范法学质疑
1.“农民工”概念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概念的特征相悖
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能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在法律制度中形成一些有助于对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现象与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与概念。9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之一,其作用在于对社会中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的并且需要法律进行规制的事实进行定性,既要确定这个事实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还要确定其法律性质。法律概念应当是精确的,具备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如果只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不能确定这个概念是否能够包含所指向的对象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所包含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合理;法律概念必须是规范的,即在语言学上和法学上都是标准的。10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社会习惯用语才能转化成为法律概念,为法律规范所确定。
现在“农民工”俨然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但双重身份下的“农民工”称谓不管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颇具争议,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没有廓清。如果没有针对进城务工农民严格限定的法律概念,我们就不能理性地去思考与“农民工”群体相关的法律问题,对于“农民工”身份界定、权益保护理论的研究和政策、法律的制定也无异于空中楼阁。现在界定的“农民工”概念,只是考虑社会舆论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性特点,而没有考虑“农民工”概念在身份角度上所体现的两可性,这就使得“农民工”概念载入法律规范之中时其界限范围无法确定,让依附于概念之上的权利义务无所适从,导致了“农民工”群体权利保障的虚置。
2.“农民工”概念与法律精神相悖
政策法规对于“农民工”概念内涵的界定包含两种:农民的身份与产业工人。其实无论农民还是工人,他们的第一身份都公民。农民本是公民,在进城工作之后成为工人,享受工人的待遇,但其仍然遭受身份的歧视,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实际上这种不合理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与“农民工”概念的指引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使“农民工”概念合法化,用法律的形式公然规定不平等的概念时,其显然偏离了现代法律的平等精神。
(三)“农民工”概念的制度法学质疑
1.“农民工”立法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损害
我国在制定相关“农民工”法规的时候,出发点是为了重点保护“农民工”的具体权益。但事与愿违,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门性立法在形式上似乎对“农民工”非常重视,但实质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以立法的形式变相地承认“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将“农民工”与公民割裂开来进行特殊对待。这反而成为一种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障碍。立法应该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而不是去区分适用对象的身份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于不断出台法规和政策,而应该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法律不适用于“农民工”的难题,这样才能走出针对“农民工”的专门立法却保护不了其权益的怪圈。
把“农民工”和普通公民同等对待,使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就足以保证其地位的平等。《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该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这里就没有所谓的“农民工”的专有概念。2011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社会保险法》中也没有“农民工”的概念。
2.“农民工”身份的现实难题
在现实中,法律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定只停留在形式层面,特别是涉及政府或“农民工”个人的利益时,“农民工”法律主体的认定就产生了争议。“农民工”进城后,应该享有公民待遇。但在许多事件中,政府、企业和城市居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仍然认定其具有农民身份,而不认可其工人身份。
四、“农民工”身份重新定位的语义规范路径
(一)取消身份歧视的称谓——“农民工”
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东西,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契约是人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对身份的根本否定。契约将人们从身份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对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尊重。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1
“身份化的社会状态正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标志之一”,梁治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正是要以契约取代身份”。12而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中,既残留了“身份社会”的身份对“农民工”的影响,又没有完全进入“契约社会”,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身份+契约社会”。13在这个特殊时期,一种隐性的身份对契约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削弱了契约对农民就业的人身保障,这样就使得务工农民因为身份原因而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农民工”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虽然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解体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等到二元社会消除以后再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这不仅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且是对现行政策的违背。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如果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不能在政策、法律、学术研究以及社会舆论中消除,那么在立法和科学研究中就有可能对“农民工”有先入为主的歧视,从而不可能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
(二)还“农民工”以产业工人身份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影响,使得“农民工”身份定位十分模糊:是农民,有获得土地的权利;是工人,就有拿工资以及享受包括年终分红、养老保险等权利。那“农民工”是什么?是为城市建设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农民?或者是工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是一个带有矛盾的复合概念,又是一个充满歧视性的概念。全社会对“农民工”的习惯称谓,让“农民工”在城镇社会日益被边缘化,要解决“农民工”不平等的身份问题,就应该从赋予“农民工”明确的身份出发,还“农民工”普通工人的身份。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把“农民工定位为普通产业工人,认为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
“工人”通常是指为挣工资而被雇用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的人,他们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获得工资性质的收入。“农民工”完全符合工人的性质。大多数“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越来越弱,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感情已比较淡薄,他们在生活方式、收入来源、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普通城市职工已经没有太多的差距。在法律层面上将“农民工”身份工人化也没有制度障碍,我国《工会法》规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可确定为职工身份。”
(三)彰显“农民工”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伴随着近现代的权利斗争的历史而产生的,是民族民主国家的产物。1789年3月,法国颁布了《人权与公民宣言》,这个宪法性文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公民权的原理和内容,就此公民身份从特权身份开始向普遍身份过渡,并对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产生了重要影响。公民权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地位,一种政治认同资源,一种履行义务和公民责任的要求,或者一种获取社会或福利服务的保证和一种取得政治权利的保证。14公民身份一般包含四种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用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身份是作为社会的个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基础。从宪法意义上来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每一个公民在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因此,确认“农民工”的公民身份,不仅是要求在法律上完成对“农民工”地位的平等保护,而且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要以“公民权利”为衡量标准和优先价值选择。
注:
1“农民工”一词,是社会大众对进城务工人员习惯性的称谓,本文为了行文过程中叙述方便,仍然使用“农民工”这个称谓,但这不代表笔者赞同用这个带有歧视性意味的概念来界定具有农村户籍但进城务工的群体。
2张雨林:《县属镇的农民工:吴江县的调查》,载《小城镇大问题》(第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29页。
3王志恺:《关于“农民工”的称谓》,《语文建设》2007年第5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1028页。
5刘豪兴:《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6[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单飞跃、范锐敏:《农民发展权探源——从制约农民发展的问题引入》,《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李广智:《舆论学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8 Cohen Robin,The New Helots:M igr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1st ed,Avebury,1987,pp 186-187。
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10张文显:《法哲学研究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1[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第97页。
12梁治平:《“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革命——读梅因〈古代法〉随想》,《读书》1986年第6期。
13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9页。
14[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单丽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5对于文化公民身份是后现代公民理论的新发展,特别是对少数族裔的文化习惯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详细内容可以参考[英]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的条件》,郭台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74-190页[加]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