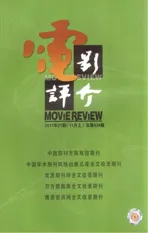《无极》,神话里的当代人生
2011-11-16王卓慧
陈凯歌曾经讲过“五年之后,你们会读懂我的作品”,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时,他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沉淀,观众可以解读出《无极》中的意蕴来。其实一部好的电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它的魅力。
陈凯歌说:“‘无极’就是我们的世界。”
这是一部有关现实、命运和理想的影片,在用电脑特技描摹出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陈凯歌试图用神话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三者的理解。无论是美轮美奂的画面,还是较多仰角镜头的使用,以及主要角色之间不纯正普通话的对白,都使影片与真正的现实镜像产生了一种间离,从而生发出一种仪式感,让影片从内在气质到外在表现形式都具有了神圣性。“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淡化了,并被仪式剧的现实所取代。”[1]而它本身实质却是“人类心灵的投影”、“世界的象征性建构”。[2]
回到影片本体,陈凯歌借用神话的表现形式和神话的叙述方式建构了影片的风格。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所有的神话都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神话的思维总是运用模拟的方式进行,把自然物放在二项对立的结构框架中,由此建构起关于世界的图像,最终达到对世界的解释。[3]在《无极》里,我们也处处看到现实、命运与理想这三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绝对的非此即彼,绝对的纯粹。当倾城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她还不懂命运;她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在现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里看来再合理不过的命:“能够得到最好吃的东西,最美的衣服,最强的男人的宠幸”,但是要付出代价:“永远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这种选择只能唯一,没有余地,没有缓冲。由此建构出了现实世界人的宿命其实也是这样:面对选择,无论多少种,只能唯一,而且一次错过,终生就再没有机会,除非“时光逆转,河水倒流,人死复生”。
从剧情来看,剧中的人物都在与命运抗争,但无论怎样挣扎,都与俄狄浦斯一样,终归逃不脱宿命,使得全剧都笼罩在希腊神话般的悲剧色彩中。光明高傲,想要与命抗争——“记着,动情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
“要是我赢了呢?”
“你赢不了!”
单单这四个字,可以看出人在命运之前再如何高傲,却根本不堪一击。陈凯歌说过:“人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宿命的,命运的确存在,在茫茫人海里遇到了某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这就是命运决定的,我的成长背景决定了我的内心深处是悲观的,比如人与人关系的相互不信任……”
在《少年凯歌》那本书里,陈凯歌刻骨铭心地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批斗父亲时,上前推了父亲一把。很多年过去,他依然为这个举动而愧疚,从《霸王别姬》、《荆柯刺秦王》到《和你在一起》他想要表达对父亲的忏悔在《无极》里依然可见。当雪国上下遭受屠戮的时候,鬼狼声嘶力竭地呐喊“我愿意”,他做了自己的叛徒。这个场面自然就能让人想到一个孩子看着父亲挨批,内心受不了煎熬,而最终上前用行动给最亲的人一击之后保全了自己,也开始做了自己的奴隶——
“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时,听到的依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就被带走了。”
——《少年凯歌》
似乎陈凯歌设置鬼狼这个角色,是借其表达自己的心声。鬼狼穿上乌鸦羽衣时痛苦的挣扎不正是他当年的痛苦煎熬吗?他在最后终于说出了心声: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但是,现在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一直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鬼狼最后羽化在空间里,有些涅磐的味道,而至此,陈凯歌也许能够为往日的行为释然一些:“就是因为我说给大家听了,我不说给大家听,我永远过不去!”在他的世界里,在经历过人与人之间最不信任的年代,他最理想的王国就是“光明洁净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互相信任友爱的地方,在那,我们可以像风一样奔跑飞翔,你是她的孩子!”但是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呢?当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与后现代主义占领和撕裂人们的生活,物质充裕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经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4]人们生存的心声在电影中通过另一个奴隶昆仑做了表白。昆仑是一个擅长奔跑的奴隶,他整日的奔跑终归被形容成“逃”!这世界每个人都在“逃”,每个人都奔波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完成工作、得到晋升,每个人都在永无止境地忙碌,没有人能有暇顾及到身边日益变化的速度,“就像风起云涌,日落月升,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婴儿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来,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爱上一个人!”在马尔库塞的眼里,人已经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忘却了意义,成了单向度的人,最终失去了自己!相比那些艰涩的哲学语汇,《无极》用美丽的语言,用较为碎片化的方式告诉观众这些简单的道理。
影片启用了日、韩、港及大陆四地的明星,及用业内最为著名的人士打造化妆及音乐,并以此为我们构建了几个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故事。从符号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些都只是影片符号的第一层表意系统,具有的是“所指意义”,而第二层次“内涵意义”,才是大众传媒传递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罗兰•巴特将这个“内涵意义”称之为“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5]。在他看来,当那个先前的能指/所指关系中产生的符号成为下一个关系,也就是神话的能指时,内涵便产生了。从本片来讲,陈凯歌就是用神话的故事,并通过神话的方式,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焦虑。故事是所指意义,表达出来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焦虑则是一种“神话”(也就是内涵意义)了。可以说,影片自始至终奉献着诚意, 用近乎宗教般的仪式感为观众打造了一个当代神话。列维•斯特劳斯评价过,神话既没有逻辑性,也没有连贯性,在创作表面上是随意的。[6]《无极》同样没有采用流行的剧情片的模式,与其相比,空间逻辑与剧情逻辑都不甚严密,从这点来说更打造了影片的神话风格。
但影片在行销时过多地渲染了其商业性的卖点,创造了极高的收视期待,而影片本身想要的表达与蕴含的哲理并不似浅显流行的商业大片,它需要用心品味。然而选择贺岁档上映,使影片严肃的主题与观众的娱乐诉求相去甚远。这种差异或多或少类似于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众所周知,在精英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召唤结构”(伊瑟尔,1970)。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曼•英加登就提出文本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有赖于读者自己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情感主动参与和阐释文本,这样作品才完满起来,意义才能显明。如此,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就成了文本的基础结构或审美对象的基础结构,伊瑟尔将其命名为“召唤结构”。 “它召唤读者把文本中包含的不确定点或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本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文本的空白召唤、激发读者进行想象和填充作品潜在的审美价值的实现,是吸引和激发读者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根据伊瑟尔的观点,一部作品的不确定点或空白处越多,读者便会越深入地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实现和作品艺术的再创造。”[7]很明显,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在传统的精英艺术中大量存在着。而大众文化要求的是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要求的是在困顿与乏味的生活之中带来一些娱乐的放松,因此,浅显流行的商业大片更容易受欢迎,相较而言,对不确定性和空白的要求就没有传统艺术、精英艺术那样高了。而《无极》对于人生存情境、心灵诉求、精神状态的关照,它的关怀气质已经让它具备了精英艺术的品格,它的不确定性与空白需要观众主动参与、思考、解读,而不是简单的娱乐诉求就可以达到的。
影片的电脑特技还不尽完美,但大画面气势磅礴,小画面细腻入微,转场自然,大部分演员的表演都比较到位。至少能感觉到这是一群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并不是一部随意把玩、故弄玄虚的作品。
五年之后,再看《无极》,看到的依然是诚意,依然是人生,依然是命运,所以还是要致以敬意。
注释
[1]劳里•杭柯:《神话界定问题》,[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2]劳里•杭柯:《神话界定问题》,[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3]转引自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4]转引自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5][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6]转引自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7]百度百科:召唤结构,http://baike.baidu.com/view/6901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