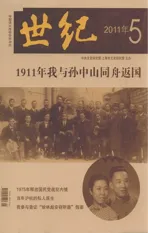寻找《掩不住的阳光》始末
2011-07-26乔争月
乔争月
(作者为《上海日报》总编助理,专栏作家,乔信明将军的孙女)
2009年12月中旬,我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父亲乔泰阳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寻找一份珍贵的手稿。他说刚刚得知我的爷爷奶奶在五十年前写了一份书稿,是关于爷爷和战友们狱中斗争的传奇故事的。这份书稿可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吴早文那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几十年过去了,知道的人也就淡忘了。当时的我真没有想到,这么一找居然找到一部尘封整整半个世纪的长篇革命历史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小说于今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读者反响强烈,短短数月已经第五次印刷了。
寻找缘起
2009年4月纪念爷爷乔信明将军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南京召开。会前,我们乔家编印了一本纪念画册,上面刊印了1958年由爷爷奶奶创作的《狱中斗争》剧本封面和1959年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求修改出版这个小说(剧本)的约稿信。
爷爷在红军时期曾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十军团)二十师参谋长,是方志敏同志最后带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和狱中斗争的见证人。
上世纪50年代初爷爷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在写自传时就记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后战斗和狱中斗争的有关情况。后来,方志敏夫人缪敏同志不断给爷爷写信,询问方志敏最后斗争和生活情况,爷爷在与她多次通信中回忆起许多往事。1956年总政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后,爷爷应邀撰写的文章《回忆方志敏同志》刊登在《解放军文艺》上,又被收入《星火燎原》第二卷。随后文稿被多家刊物转载,甚至刊登在越南人民军的刊物上。

1959年夏乔信明于玲夫妇合影照片
1958年爷爷阅读了方志敏著作《狱中纪实》非常激动,撰写了《读〈狱中纪实〉后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之后又在南京军区文艺创作组长王昊等协助下,与我的奶奶、新四军老战士于玲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狱中斗争》。这个剧本定名为《狱中斗争》,可能是受了《狱中纪实》的影响。
我的伯父、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参加爷爷纪念活动回京后,把这本印有《狱中斗争》剧本封面的画册送给了陈丕显长子陈小津。作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和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的陈小津,热心研究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看到画册上的剧本封面后建议搞影视创作,后来又提议出版这个剧本。由于剧本只有几万字,我们全家决定再增加一些回忆文章和采访材料。
为此,2009年12月中旬父亲乔泰阳和母亲曾红到当年协助创作的王昊家拜访,希望找到一些当年的采访素材。爸爸说王昊爷爷年老体弱,但谈起往事又神采飞扬。他说虽然自己当时没有采访记录,可是1959年在黄山配合爷爷奶奶创作了一部小说手稿,主要是爷爷口述经历,奶奶执笔写作的。问起手稿下落,他说应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那里。
寻找历程
我在英文报纸上海日报社工作,用英文撰写一个介绍上海历史建筑的专栏,以挖掘建筑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故事为亮点,很受外国读者欢迎。因为职业原因,所以联络找人和调查历史背景我都比较擅长。
接到寻找手稿的任务后,我马上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组织人事处联系,又向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同志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年事已高的吴老编辑4月份生病住院,已经无法讲话了。所幸他的夫人袁奶奶身体还可以,住在家中,但年纪也很大了。2009年12月16日的晚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来到了她位于天钥桥路的家。
由于素昧平生,站在吴家楼下我心里有些忐忑,而且我也不清楚那份手稿到底是什么内容,几十年都过去了还能否保存完好,能否找到呢?不过一打开门,见到的吴夫人面目慈祥,个子不高,微卷着银色头发,看得出年轻时长相清秀。她在电话里就说一口上海话,所以我特别叫上我的先生、上海人陈贤一起去,算做“翻译”吧。
吴家房子不大,陈设简单,但干净舒适。客厅兼卧室的墙上挂着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将军给吴老的一副题字“为人民服务”。老式柜子上放着吴老的几张合影照片,浓眉大眼,看起来气宇轩昂。
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吴夫人找出两个很旧的大牛皮纸袋,里面装满了厚厚的手写稿件。纸袋上还写着我爷爷乔信明的名字,不过笔误写成了“乔明信”。吴夫人说吴老住院前已经有些糊涂,但状态好一些就惦记着这份手稿,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看看。吴老让她有机会一定要交到乔家人手中,因为是“人家辛辛苦苦写的”。

1939年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左一)与所属老六团领导人合影。右一为乔信明
吴夫人还拿出了一封写给我大姑姑乔阿光的信。信上写道:吴老已84岁了,患有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但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再说这是王昊托付的事,是人家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要负责看护好稿子,天天还要拿给他看。她想把书稿交给乔家,但是她年纪大了这么厚重的书稿既拎不动也不知如何邮寄,十分犯难。这封很重要又很感人的信件一直没有寄出。我一看写信的日期,居然是2007年12月;再看看内容,顿时有种“很历史的感觉”。
初次见面的吴夫人还带我们去参观了家里的“书库”,也就是位于同一楼层的一个小套房子。“书库”几个大书橱陈列了吴老编辑过的军事历史题材书籍,其中有不少包括陈毅和刘伯承等知名将领的传记。她说这就是吴老的世界。而爷爷奶奶写的手稿就一直放在一个黄色玻璃书橱前的纸箱里,静静地躺了这么多年。两位老人对待事业的认真态度,特别是对朋友所托事情的责任感让我十分感动。
不过更有历史感的还是这份手稿。回家后我打开牛皮纸袋取出手稿,发现居然是多年不见的格子稿纸,而且比我儿时用过的那种看上去还要“原始”。每一章节的稿子是用白线仔细缝订好的,还认真地用杂志纸做了封面。杂志上竟然还是西班牙语的,这是古巴出版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杂志,很有时代特色。
更让我惊讶的是手稿居然是一部地道的长篇小说,叫《掩不住的阳光》,是爷爷奶奶1959年夏天在黄山写就的。我真没想到作为老革命家的爷爷奶奶居然还创作过小说。此时,我更加意识到这份手稿的历史价值,这是爷爷奶奶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于是,我在2009年12月的平安夜,亲自把稿件送到父亲手中。虽然手稿很重我也不敢托运,而是把这两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放在手提行李里,几乎是抱着带到了北京。
创作经过
原来1959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发来约稿信,希望爷爷奶奶能把几万字的“小说初稿”《狱中斗争》进行修改以便出版。爷爷奶奶深受鼓舞,也受到启发,因为约稿信把电影剧本《狱中斗争》称为小说,他们就考虑怎么在这个电影剧本的基础上编写长篇小说。
经过一番准备,这一年夏天他们邀请当年狱中难友、时任江苏省军区政委曾如清将军和军旅作家王昊同上黄山。据说,一到黄山,爷爷就把大家带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打仗的旧战场,讲述当年战斗的情景。此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要到黄山搞创作。在这个既触景生情,又安静宜人的环境中,亲历者回顾述说指点,执笔人加班加点突击,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小说初稿,定名为《掩不住的阳光》。多年后回忆这次黄山行,我父亲说他们由于当时年纪尚小(他还不到十一岁),只顾着在山上游玩,一点也不知道父母是在写小说。而我大姑姑乔阿光还依稀记得奶奶当年常常多思失眠,辛苦地查字典寻找词汇,估计就是在准备创作这部小说。
从黄山回到南京后,爷爷住院看病,奶奶上班工作,就把小说手稿交给王昊整理出版。没想到后来出现了不少意外:1963年爷爷不幸因病逝世,年仅54岁;1966年又发生了“文革”,王昊同志先是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后来又调动工作。在“文革”期间,此类题材作品是要受到批判的,他冒险把小说手稿保存在了家里。

《挡不住的阳光》原稿找到时的原状
“文革”结束后,王昊把手稿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整理出版。吴老用针线把手稿装订成册,认真整理。由于他分管的是“将帅传记”丛书,因体例不合没有编入丛书,他们家就一直精心保存这部手稿达三十多年。
我的奶奶
可以说,没有我的奶奶于玲,就没有这本精彩的小说。
大家闺秀的奶奶是个有才华的奇女子。小说出版后许多人都说,如果爷爷没有遇到有文化的奶奶,不把他的传奇经历变成文字,那么爷爷的传奇经历也就随着历史变迁散落了……
奶奶名校毕业,投身革命,一生历经战争的考验,我爷爷早逝的悲伤,“文革”的迫害和严重疾病的折磨,却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精神,多次大难不死,越活越精神,越活越精彩了。与旧时传统女子不同,她很有个性,极有主见,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她特立独行,从不逆来顺受,不转弯抹角,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教育子女上,她也和“非严厉就溺爱”的大多中国家长不同。她对子女比较宽松,家中没有太多规矩,让他们“野生野长”自然发展,儿女们最后也个个成才。
印象中奶奶总是穿鲜艳的大红衣服,很搭配她雪白发亮的头发和自信满满的表情。她的自我感觉总是很好。2008年春节她在病房里跟我回忆起少女时代上美国教会学校的故事。她说班主任是个美国人,一天清晨上课前用英文夸她“Christina, how beautiful you are!” (克里斯缇娜,你真美丽啊。)浓重的美音从90多岁的奶奶嘴里说出,吓了我一跳。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奶奶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看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无论穿短袖旗袍坐在大草坪上,还是和几家世交奶奶们的合影,她也许并非很美丽,但绝对是看上去自我感觉最好的。2007年深秋我去家里探望奶奶,她还说“我是从小观园里走出来的”。由于她的母亲早逝,奶奶小时候被送到亲戚家住,那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祝园。但在这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从弃官从商的实业家四姑父那里长了不少见识。奶奶说每次四姑父外出办事回来都会跟她说说旅途见闻,这些都为她不寻常的一生打下伏笔。
再说我把《掩不住的阳光》手稿送到北京后,父亲一看发黄发脆的稿纸上多数都是奶奶于玲的笔迹,感慨万千。为保护手稿,陈小津董事长帮助安排4台复印机抓紧复印,又安排6名打字员对照复印件制作电子版。
此时的我们再也没有想到,远在南京的奶奶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她的病情在2010年元旦后急转直下,爸爸和伯伯急忙带着手稿赶到南京看她。但是奶奶的心脏已经十分脆弱,为怕引起她激动,手稿的事情一直没有告诉她。这份离开她整整半个世纪的手稿就在病房里静静陪她度过了人生最后四天时光。

奶奶的生日是正月初三。每年春节的初三,南京天目路老房子的大客厅里都挤满来祝寿的人。吃完寿面后,她指挥来宾大合唱,唱《新四军军歌》等一些革命歌曲。她指挥动作有力,满脸自信的笑,个子虽小却迸发巨大的活力和能量。
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这些歌曲的含义和爷爷奶奶亲历的战火岁月。在追悼仪式现场,这熟悉的激扬旋律又响起了。看着密密麻麻花圈上的名字和密密麻麻排队来看奶奶的故交们,我好像突然懂了。而这份手稿对我们全家人来说就更是一份珍贵的回忆了。
最后一次见到奶奶是她去世前三天,病重的她躺在病床上。与一般危重病人虚弱放弃的表情不同,奶奶双目灼灼,表情坚定,依然充满着一种战斗的力量。不甘心,不放弃,直到最后。那个表情,我永远不能忘记。
“妈妈的一生,是光彩照人的一生。” 追悼仪式结束后,爸爸他们用这个词来形容奶奶的人生。如今想到奶奶,就想到2009年生日友人送她的一幅字画。大红的纸上写着“最后的玫瑰”,末了还画着一朵娇艳的红玫瑰。 奶奶93岁的人生也可以浓缩为一朵带露带刺的玫瑰,如此地鲜红美丽,光彩照人。
一点感想
实话实说,我一直把寻找手稿当成父亲交待的任务。这个任务我圆满完成,也就高高挂起了。小说出版后我一看那么厚,我工作又忙,就迟迟没有认真捧读。对小说的了解全都来自反复研读整理多遍的父亲。
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偶然有闲我翻了翻,居然被深深吸引了。原来这部小说和有些空洞说教的红色作品不同,以爷爷和战友们的亲身经历,特别是鲜为人知的狱中生活为原型的,让人读来感觉很多细节真实可信。比如狱中每天两顿沙石饭和烂菜汤的恶劣饮食,还有敌人种种富有“创意”的折磨方式。小说的语言也相当生动,很吸引人,对各色人物的刻画活灵活现,这让我不得不佩服并非职业作家的奶奶。而情节设置也扣人心弦,让本来打算稍微翻翻的我读了一章又一章,一口气看完了大半本书。
不想说很多大道理,但是看到年仅26岁的爷爷在狱中受的苦难和考验以及他机智冷静地对敌斗争后,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来自这个我从未谋面、照片上看总是坦荡微笑的爷爷的力量。年纪轻轻的他居然能忍受那样的折磨整整三年而不放弃希望,最终斗争胜利,走出监狱投入抗日战场。
文字和历史都是神奇的。这部小说如“蒙尘的珍珠,”在上海一隅“雪藏”了几十年,又由我亲手找到失而复得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时候想想之所以能够顺利寻找到这两包沉甸甸的书稿,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件事情无法找人代办,只有我们乔家人亲自来做,而我又正好在上海工作,又擅长联络,所以虽经周折,但还是在惊喜中顺利完成这次寻找历史的任务,收获了这份无价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