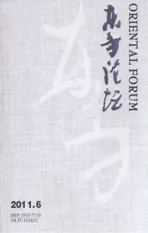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回顾与展望
2011-04-03王委艳
王委艳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回顾与展望
王委艳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话本小说研究已经走过90个年头,回顾九十年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话本小说研究划分为开创、深化、总结和繁荣突破四个时期。话本小说研究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边界、方法、成果、研究者队伍等一系列要素的“话本学”学科。但研究依然存在缺乏深度模式、理论总结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文艺学的立场,话本小说未来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口头艺术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传统文化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话本小说的接受问题研究。
话本学;话本小说研究;研究分期;研究范式;展望
话本小说的研究有赖于中国近代的小说革命和“五四”的新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P50)小说逐渐从中国文学历来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走向文学的中心。1920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为学生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1923年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话本小说遂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自此,一些在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几百年的中国古代优秀话本小说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鲁迅先生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他所见的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仅三言二拍选本《今古奇观》和《拍案惊奇》(即“初刻”),而代表话本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及“二刻”在国内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了。但自此话本小说的研究随着话本小说在海外的不断被发现呈现出繁荣局面,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研究者队伍不断增大。新世纪以来,话本小说研究的深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研究的范式、宽广度都大大超过以往。涌现了大量的专门研究话本小说的专著和期刊、硕博论文。自鲁迅始至2010年,话本小说研究已经走过90个年头。本文拟从话本小说研究的分期和研究范式二个方面对90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对话本小说以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话本小说研究的分期
话本小说研究的分期和小说观念、学术环境、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学术文章、专著的出版情况,笔者大致将话本小说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开创时期(1920年代—1940年代)
上面述及,由于中国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才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小说地位的提高直接影响了小说研究的兴起。话本小说由于长期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打压,很多已湮没不闻。因此,这一时期是话本小说的整理收罗和初步研究阶段。开创话本小说研究先河的是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以五章的篇幅介绍了从宋元话本到元明讲史再到明拟话本小说,把话本小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鲁迅先生对“话本”、“拟话本”的定义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话本研究者。对于“话本”,鲁迅写道:“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依凭,是为‘话本’。”[2](P73)由此,“话本指说话人的底本”这一定义广为接受。对于“拟话本”,鲁迅先生并没有给出确切定义,只写道:“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习俗浸润,乃及文章。”话本与拟话本概念的提出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即话本与拟话本在接受者、承继关系、文本艺术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质。同时,鲁迅还把话本提高到了与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同等的地位,为以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
胡适先生这一时期也有论述话本小说的文章,作有《白话文学史》等。在为1928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宋人话本八种》做的序中,对话本小说的分类、体制均有论述。比如对话本小说头回的辨析很有见地。鲁迅先生对话本小说“得胜头回”的解释为:“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2](P77)胡适则从另一角度对之进行了辨析: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3](P465)
这一时期对话本小说研究用力最勤的另一位是郑振铎先生。郑先生除写有《宋人话本》、《明清两代的平话集》等文章来介绍话本小说外,1930年代初分章发表于不同刊物的论文《宋元明小说的演进》还对话本小说的演进进行了独到的论述,在论述宋人的短篇话本小说时,作者写道:
宋人的短篇话本,就今所传者观之,其运用国语文的技术,似已臻精美纯熟之境。他们捉住了当前的人物,当前的故事,当前的物态,而以恳恳切切的若对着面的亲谈的口气出之,那末样的穷形尽相,袅袅动听,间或寓以劝诫,杂以诙谐,至今似乎还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可爱。难怪当时这些说话人是如何的门庭如市了。这些说话人虽是职业的,我们疑心他们决不是似通非通的“艺人”,而是很有天才的沦落的文人。或者他们只是口说着,而编辑这些话本的,却另有其人在。这些话本,或经过好多次的润改也难说。[4](P138)
郑振铎先生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可贵的是,郑先生在该文中还论及除“三言二拍”外的其他话本小说,比如《三刻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这对于扩大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郑振铎还在其他文章里不断论及话本小说。
这一时期,蒋瑞藻、孙楷第、赵景深等也有研究话本小说的论文行世。如蒋瑞藻出版《小说考证》中涉及了部分话本小说之源流、孙楷第先生的《三言二拍源流考》、《小说旁证》,他们共同开启了话本小说源流的考证研究。孙楷第还发表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开启了话本小说的书目学研究;赵景深先生也发表了《小说闲话》、《中国小说论集》等,对许多话本小说进行了考证。
纵观这一时期的话本研究,我们发现,除了对话本小说的收集、整理、出版的业绩外,对话本小说的研究已经从多个方面奠定了基础,史学研究、形式研究、来源、考证、目录等等方面均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深化阶段(1950年代—1960年代)
除了“文革”十年,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研究在解放后和“文革”前出现了一个深化阶段。除了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中把话本小说进行专门讲解外(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均对话本小说给予高度评价),话本小说的整理出版也蔚为大观,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这一时期研究话本小说的学者基本来自“五四”时期,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化自己的研究。
郑振铎1953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小说传统》探讨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短篇小说的分类,即传奇文和平话两种,后者即为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这种提法很具有学术价值,它指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两种不同形态,使古典小说研究的格局与思路为之一新。
谭正璧先生1961年发表《三言二拍资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书中详细考证了“三言二拍”的故事来源,为研究话本小说的历史、叙事、艺术等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遂成为研究“三言二拍”的工具书。谭先生的另一本书《话本与古剧》开辟了研究话本小说的另一条道路,即从中国古代戏剧、曲艺与话本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
这一时期,孙楷第先生发表《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一书,从俗讲、说话等口头艺术与白话小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本时期还有李啸仓《宋代伎艺杂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陈汝衡《说书史话》等等。
本时期在“五四”时期话本研究的基础上,随着话本小说的挖掘、整理、出版,资料极大的丰富,话本研究呈现出深化局面,一些新的研究角度的产生深化了话本研究。
(三)总结阶段(1979年代—1990年代)
从“五四”到1980年代,话本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话本小说不断的被整理出版。话本小说作为一个清晰的文本类型,其作品、发展脉络、艺术形式等已经清晰地展现在研究者的面前。资料的丰富预示着一个总结阶段的来临。
1980年,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出版,胡先生为此书费尽心血,历时13载,三易其稿,八十余万言。该书被赵景深先生称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5](P5)该书集考证、史料、艺术分析、叙录于一身,是研究话本小说者绕不过去的总结性著作。胡先生1981年还出版有《苑春杂著》,书中对“说话”进行了考证,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规律、体制进行了总结,还分析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2篇话本小说。
本时期,除了老一辈学者如孙楷第、程毅中、谭正璧等有论文、论著发表外,出现了一批新人,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对话本小说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如张兵《话本小说史话》(1992)、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等。他们的研究以“话本小说”类型为基础进行话本小说自身规律的探寻。这就避免了过去文学史以朝代为单位的文体发展的“割裂”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类史”。这无论从“话本”文类的连续性还是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性来说都是话本小说研究的一种总结性深化。
本阶段还出现了以作家为对象的研究专著,如缪永禾《冯梦龙和三言》(1979)、陆树仑《冯梦龙研究》(1987)、马美信《凌濛初和二拍》(1994)、黄强《李渔研究》(1996)等;以及以作品为对象的专著,如徐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以小说类型为对象的研究作品,如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1993)等。这些作品从作家、作品、类型等角度研究话本小说,研究大大深化,对作家、作品及类型进行了总结。
纵观这一时期,总结性研究是最大特点。但应当看到,研究思路还依然很陈旧,理论性总结缺乏,宽度、深度还依然没有逃脱“五四”模式。因此,话本小说研究酝酿突破。
(四)繁荣突破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话本小说呈现出繁荣局面。西方文论的译介为话本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研究话本的专著、期刊论文较前几个阶段更加丰富。比如从中国知识网(CNKI)上按照“摘要”检索项,输入检索词“话本”,1979—1999年,共有930个结果,且都是期刊论文;而在2000—2010年期间,共有1022条结果,其中期刊论文778篇,硕士学位论文203篇,博士学位论文41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话本小说研究呈现新的研究视角。比如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2002)、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2002)把西方叙事学理论运用于话本的研究。比如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小说结构三个方面对话本小说进行艺术性分析,从而发现话本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质。另外还有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2009)、温孟孚《“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等不同程度的运用了西方文论。
从时代更易的角度研究话本的如朱海燕《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变迁》(2007);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话本的如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2008);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话本的如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从文体学角度研究话本的如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2006);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话本的有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以作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有聂付生《冯梦龙研究》(2002)、冯保善《凌濛初研究》(2009)、胡元翎《李渔小说戏曲研究》(2004);以及以作品为对象的研究如雷庆锐《晚明文人思想探析:《型世言》评点与陆云龙思想研究》(2006)、常金莲《〈六十家小说〉研究》(2008);从文献学角度研究的如陈桂声《话本叙录》(2001)等等。
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话本小说研究呈现出繁荣局面,一些新的研究角度不断开拓,除了上面一些专著提示的研究方向外,笔者还对大量的期刊论文进行了分析与分类,大致的研究角度为:考证、叙事学、语言学、文体学、人类学(如“母题”、“原型”研究等)、性别、禅宗、商业、民俗、美学、道德伦理、插图等。由此可以看出,话本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范式、方向的多元,边缘性研究的拓展繁荣了话本的研究。
值得关注的另一种研究范式是艺术总结性研究,即从话本小说的文本现象出发总结话本小说独特的叙事规律。如鲁德才先生《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2002),从白话小说形态的角度总结其艺术规律、发展脉络。这是一种由小说到理论的研究范式,与由理论进入小说是有着根本的不同。但鲁先生的著作执着于小说形态史的梳理,建立具有民族特色小说理论的意识方面还是稍有不足的,因此是非常遗憾的。
纵观以上四个阶段,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背景,第一阶段仰仗小说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在话本小说收集整理出版以及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第三阶段随着大量话本小说收集整理出版,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第四阶段则是在西方理论译介的背景下,研究角度为之一新。
二、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话本小说研究的繁荣离不开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话本小说研究的发展过程就是研究范式多样拓展的过程,从上面的研究分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下面笔者就话本小说研究的几种基本的范式进行分析。
(一)史学研究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开启了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的先河,他开辟的小说史研究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史研究。鲁迅先生的研究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的影响:
1.专门史研究。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时间为经进行史学梳理,使小说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2.分类史研究。鲁迅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在类型上的划分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神话传说、传奇、志怪、话本、拟话本、神魔、人情、谴责等。
3.以朝代为时间序列的分期研究。鲁迅的研究在以上2种特色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以朝代为阶段的分期研究,使小说在各个朝代的特点非常直观的展现出来。
郑振铎在小说史研究方面也有精到论述。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小说传统》中,首先对中国小说类别和特质进行了总结,然后以朝代为时间单位对各个朝代的小说类型和特色进行了论述,其研究无疑也具有示范意义。
从话本小说研究的实际可以看出,以“话本小说”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史”研究是话本研究的一大特色。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无疑具有开创性。石麟《话本小说通论》中的“类别论”把话本分为风情、市井、信义、公案等等类型,除了有话本本身类型的影响外,无疑受到鲁迅的分类史研究的影响。另外,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下编对话本小说的叙事类型分析亦如此类。另外,以朝代为时间序列写话本小说史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从宋代至清代写出了各个朝代话本的不同特色。
(二)考证、文献学研究
话本小说湮没既久,很多话本小说都经过曲折的发现、考订过程,因此,考证、文献学研究成为话本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而且这种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研究,它为其他研究范式提供了资料支持。许多学者都做过考证方面的工作,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胡士莹、赵景深、谭正璧等。
孙楷第先生《三言二拍源流考》、《小说旁证》;谭正璧先生《三言二拍资料》等都是话本小说来源的翔实考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集多项研究范式于一身,不乏考证、文献学的研究。后来学者陈桂声《话本叙录》是一本话本小说文献学研究专著。这方面的研究即使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方面,文章不断见诸期刊,比如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王瑾的《“三言”、“二拍”本事来源的新发现》等。
(三)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话本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可分为三种类型:1.以作家为对象的研究;2.以作品为对象的研究;3.以小说类型为对象的研究。个案研究弥补了小说史研究太过笼统的弊端,有利于对作家、作品、类型做深入的分析,从中发现个案的独特性。近年来随着话本小说研究的深入,个案研究呈现增多趋势,尤其是大学中国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尤其喜欢做针对性很强又较易操作的个案研究。这方面已经出版许多专著,诸如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冯保善《凌濛初研究》、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顾克勇博士论文《陆文龙、陆人龙兄弟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以作家为对象的研究;常金莲《〈六十家小说〉研究》、温孟孚《“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胡莲玉博士论文《〈型世言〉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的以作品为对象的研究;以及以小说类型为对象的研究,如苏建新博士论文《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廷兴博士论文《明清艳情小说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四)文体学、语言学研究
话本小说的文体学虽然在话本研究中比重较小,但却是很有特色的。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对话本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影响予以了史的考察,从文体的角度论述了话本的形态。张永葳《八股文对拟话本文体的塑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则独辟蹊径,从结构逻辑、叙述方式、细部述写方法等方面考察了八股文对拟话本文体的影响。
从语言学方面对话本小说的研究虽然鲜有专著,但从发表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来看较为活跃。比如李淑霞硕士论文《〈清平山堂话本〉动态助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英硕士论文《明话本小说动词重叠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出版)、高玉洁硕士论文《〈清平山堂话本〉介词研究出版》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五)理论分析研究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扩大了国内研究者的视野,运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研究模式,并且这种理论分析研究模式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表现在话本小说研究上,从大量用西方理论分析话本小说的专著、期刊、硕博论文可以看到西方文论的影响。具体理论如叙事学理论是运用较多的分析工具,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以及其他文学史研究、个案研究均不同程度的运用了叙事学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也是话本小说研究者常用的分析工具,刘果《“三言”性别话语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专著,期刊论文更多。运用接受美学研究话本小说的如吴波《明清小说创作与接受研究》。用经济学理论对话本进行“边缘性”研究的如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很有特色。
不同于以上的“理论—作品”研究模式的另一种理论分析研究模式是“作品—理论”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具有理论生产的特质。立足于话本小说,总结话本小说叙事、形态的规律与发展脉络。这种研究很具有知识生产(理论生产)的性质,很值得我们关注。比如鲁德才先生《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就对白话小说的艺术形态进行了总结,比如对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两个不同的发展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形态学探讨;对白话小说横向发展系统、民间说书与白话小说交叉互动等方面进行了小说形态形成、演变的探索。张勇《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白话小说叙事的独特性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遗憾的是,这些探索虽然总结了一些叙事规律,但没有形成中国独特的叙事理论,工具性较西方文论贫弱许多。
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并非以上5类所能穷尽,但上述分类在话本小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值得指出的是,话本小说研究往往是一种综合的劳动,是以上诸种研究范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含、相互补充,形成了话本小说研究的综合性特征。
三、话本小说研究展望
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来,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它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成果、研究者队伍等一系列作为一个学科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果将之命名为“话本学”也是恰当的。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话本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已经相当成熟。从研究者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划出一条脉络来。以上仅仅是比较纯粹的话本研究者和作品,如果加上中国文学史、介绍性的著作(如石昌渝《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方面的研究者和作品,则话本小说的研究队伍会更大,作品会更多。但仔细考察话本小说的研究状况,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极大的危机,大量重复性研究浪费了研究者的许多精力。张兵在1992年《贵州文史丛刊》第1期上曾发表文章《话本小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出变革话本研究方法的主张,并提出4条主张:“(1)用历史的、美学的眼光;(2)古为今用的原则;(3)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4)坚持纵横交错的比较来研究话本小说”。由以上论述可知,张兵的主张已经不同程度的得到实现。而现在距张兵的文章发表已经过了18个年头,话本小说研究今非昔比。经过了新世纪10个年头的繁荣,结合国外文学研究发展的情况,不难发现我们的研究有些方面还非常不足。如果从文艺学的角度考察话本小说的研究,更让人感到匮乏。缺乏深度模式、理论总结能力的欠缺、金圣叹式的知识生产凤毛麟角、总结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传统叙事经验、规律的作品更是稀有。因此,话本小说期待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艺术规律的探索,以形成自己民族传统特色的叙事理论、小说理论等。下面笔者想就自己的思考,对话本小说研究做一下展望。
中国古代“说话”艺术是经过千年发展的艺术形式,其言说、叙事的方式直接影响了话本小说艺术特征的形成。因此,从口头艺术的角度来研究话本小说无疑是自然的事情。话本小说许多独特的叙事特征与说话艺术有着直接的承继、改造、演进关系。比如,发源于“勾栏瓦舍”的说话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与听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其“交流性”特征渗透到说话的方方面面。其文本形制,入话、头回、议论、叙事无不打上“交流”的印记。以此为基础我们发现来源于说话的话本小说从结构、叙事方式、语言到意识形态无不具有这种“交流性”。这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叙事类型与叙事方式。从此出发,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从一开始的“说——听”叙事交流模式,逐渐向“写——读”交流模式转变,揭示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无疑会对由口传到书面的艺术发展规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这已经不仅仅是对话本小说有意义的事情了,恐怕会对有类似情况的文学样式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此为话本小说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话本小说研究的方向之二是传统文化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话本小说作为被底层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作为转而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之作,其流传既久,与传统文化对话本小说叙事的影响乃至操控有着密切的关系。揭示传统文化在话本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形态无疑会对其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找到答案。话本小说,尤其是具有极高艺术成就的话本小说流传至今千年不衰,即使今天仍然可以从中国古典戏剧、电影、电视剧中、民间曲艺、甚至老百姓的口头发现其踪迹。传统文化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因子已经渗入话本小说叙事的骨髓。比如中国的婚姻制度讲究门当户对、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等,话本小说写这方面的很多,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了两种叙事模式,其一是遵从式文化叙事;其二是背反式文化叙事。经过细致的文本细读,我们发现话本小说在妇女问题(比如贞洁观念等)、婚姻问题、商贾问题等方面尤其喜欢采用第二种。由于叙事与婚姻制度的背反所产生的喜剧性或悲剧性在话本小说里非常常见。比如李渔《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其构思的巧妙不但表现在“戏中戏”的小说结构,而且还表现在由于婚姻制度所导致的戏里戏外的张力关系,并由于这种张力关系而形成的故事动力系统。而对于忠孝节义等问题上尤其喜欢采用第一种。另外一些话本小说表现善恶因果、命相观念等则采取了两种叙事兼备的方式,使叙事体现的文化观念更具有辩证特征。这些情况在话本小说中非常普遍,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叙事”。
话本小说研究方向之三,笔者以为应把接受者考虑进去。以上论述可知话本小说承继说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交流性,交流是一种双方行为,只考虑一方显然是片面的。考察话本小说的接受问题应该成为话本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话本小说研究者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发现,话本小说作者、叙述者、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可以通过文本叙事的各种现象表现出来,比如公案小说的叙事模式之一是先叙述案件的发生过程,然后进入审案程序,这种叙事结构表现出很强的交流性,即叙述者把读者置于“观众”的位置,官员审案的过程由于读者已经明了案件的全部过程而具有当众表演的性质,这样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读者与故事之间的间离状态,这种间离因避免了接受者沉湎故事而具有娱乐性的特质。类似的情况、相反的情况、或兼具二者的情况在公案小说里普遍存在。由此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的读者交流与西方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揭示这种不同就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本接受理论。研究话本小说的接受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本接受的“可靠性”问题,这在西方修辞叙事学理论中到目前依然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探究话本小说的接受问题时同样会出现具有挑战性的状态,如由于历史的、观念的、地域的流转而形成的“可靠性”的历史性问题等。在此由于本文论题所限,笔者不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总之,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成绩斐然,但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尤其是从文艺学的学科特点来考察话本小说的研究,其局限与不足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需要我们站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前沿考察我们自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知识生产机制,就像我们的前辈金圣叹、王国维、钱钟书那样。一味的跟风丧失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1] 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胡适.胡适文集: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5]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潘文竹
Ninety Years' Study of Venacular Novels
WANG Wei-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study of venacular novels has gone through 90 yea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initiation, deepening, summary and prosperity. This field of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its own object, boundary, methods, achievement and research teams. There are weaknesses in this research, however. For future researchers, there are thre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y can push forward their task: verbal art and narr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rrative; reception.
study of venacular novels; research period; research paradigm; outlook
I207
A
1005-7110(2011)05-0108-06
2011-02-21
王委艳(1977-),男,河南内黄人,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