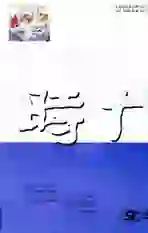走出父权制的陷阱
2010-06-28杜洪晴
杜洪晴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灰姑娘》的三个不同版本,探讨了父亲缄默和缺场的深层次原因,以揭示隐藏在背后的父权制陷阱,即企图掩盖男性第一性,女性第二性的社会不公的预谋:父权制通过将女性形象符号化和恶患化,迫使女性同母性世界分离,从而投入文权世界的保护。
关键词:父亲;缄默;缺场;父权制陷阱
经典童话《灰姑娘》自问世以来,几经流传变更,魅力依旧。在现存的几百个版本中,其女性形象,如善良美丽的灰姑娘,凶恶狡诈的继母,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形象,却异常沉默甚至缺场,使人顿生疑惑,难道这是一部表现女性话语的文本?带着这种疑问,本文将目光转向三个《灰姑娘》版本,通过分析父亲缄默和缺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父权制的陷阱。
一
写于17世纪的巴斯尔(Basile)的《猫女灰姑娘》描写了一个性情变化无常的父亲。开始,他对女儿极尽宠爱,但不久就把她抛诸脑后,把所有的爱转移给继女们。而人们却将这位父亲的错归咎于继母和其女儿们,这正是父权机制赋予他的优越和特权。杰奎琳·M·斯科特曼在一篇论述继母形象的文章中指出,女性往往通过向男性施加影响来获取权力,继母试图在婚姻中寻求男性的安全和爱护,以赢得通往权力的途径。父亲的冷漠无情和女性世界的暴力仇视使灰姑娘不得不转向另一位男性寻求安全。最终,国王将灰姑娘从继母的虐待折磨中解救出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给人一种假象,男性世界比女性世界更加安全公正,女性只有求助于男性才能获得永久的幸福。
二
19世纪格林兄弟的《阿斯普托》(Ashputtle)是现今流传最广的一个灰姑娘版本,女主人公阿斯普托同样受到父亲的冷遇。出差回家的父亲给继女们带来漂亮的衣服、珠宝,却只带给阿斯普托一棵小树枝。小树枝是“潜藏的智慧,神圣的灵感,以及大地之母超自然力量的象征”,它代表阿斯普托去世的母亲从天国带给她的关爱。但慈爱的母亲是远远不够的,在男性中心文化期許的幸福中是没有母亲的地位的,她势必构成对男性至尊地位的威胁。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吕丝·依丽格瑞指出,男权文化和象征秩序不仅压抑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潜能,也造成了女儿的放逐,因为她通往母亲/女人之路从幼年时就被生生切断,自我认同女人的潜能也被切断,更没有其她女人可以认同,只能重复位置性的自我置位,即以替代母亲的位置来自我置位于男性象征系统。母亲的早逝,为女儿进入男性世界扫除了第一个障碍。父亲是“传统、文化和意识发展的承载者”。父亲的存在使女孩认识到另一性的存在,并激起她的性别意识。女性主义学者杨丽馨也认为“与母亲分离成为女性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只有经由浪漫的男女之爱,方能获得女性身份,完成女性使命”。
故事中当王子追踪阿斯普托到鸽子房下,父亲遂毁掉鸽子房,砍掉梨树。鸽子和梨树在西方文化中都是母性的象征,毁掉它们,隐含着父亲意欲切断女儿同母性世界联系的企图。斯科特曼对此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女性气质的吸引力必须在她离开父亲投向另一年轻男子之前消除掉……他(父亲)的失落感将激起他的愤怒和仇恨。足以创造出一个‘继父形象”。父亲出于嫉妒,毁掉鸽子房和梨树,由此引出一个敏感的话题一一父女之间的乱伦之爱。根据玛丽,华纳的研究,父女间的乱伦现象很早就出现在一些童话故事中,如《圣迪姆普娜》(Saint Dympna)、《驴皮公主》(the“Peau d,Ane)等,但在现代童话故事中却消声匿迹。父亲从对女儿百般疼爱到冷眼相看可视为他潜意识里逃避乱伦的努力,斯科特曼就父亲的冷淡态度列举了三种形式——“取笑她们的女性魅力;过度严肃;冷漠绝情”。111500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亲对女儿的美丽和美德、对其遭受的虐待都视若无睹是想摆脱对女儿的性欲望,以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尊严。
故事以王子英雄救美圆满收场。此时,灰姑娘正需要一名男子将她从恋父情结中解脱出来,以社会公允的方式获得女性身份,王子发挥了父亲无法发挥的拯救作用。“背离母亲(女性)一一由主动趋向被动一一转向父亲(男性)”,同杠勘正是依循这种模式,灰姑娘才最终获得了女性身份。这种模式化的故事结构是父权机制用来界定性别文化身份和秩序的标准,旨在创造符合男性利益的两性神话。
: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50年代迪斯尼版的(灰姑娘)。父亲从故事里完全缺场,女性的家庭争斗成了故事发展的主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现实。战争期间,男子应征人伍,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但战后,男人因其努力受到嘉奖。获得原来的工作,妇女却在当时社会“返回家庭”口号下,退回到家庭的牢笼中。在故事中父亲完全缺场和继母等的横行无忌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享有更多的权力。其实女人夺权的努力注定会遭到父权社会的压迫,而父亲的缺场也另有深意。首先,他无须为女儿遭受的迫害承担责任,死后仍保有慈父的美名,赢得女儿的爱戴,而继母和她的女儿们也能把罪恶发挥到极致。其次,父亲具有男性与生俱来的权力,不屑介人家庭中女人间的争斗,而女人却不得不为这少许权力明争暗斗,但继母等恶势力最终受到惩罚暗示我们:女人对权力的欲望将给他人和自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女人只有压制这种欲望,安分守已,才能成为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这正是父权文化长期以来向女性灌输的思想。再次,无论缺场与否,父亲的影响力始终如一,他在女儿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和父权社会强大的外在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女儿,挣脱女性世界,投入男性世界的保护。
此外,故事的叙述还呈现出过分简单化的痕迹。女性关系表现出嫉妒、迫害、争斗的单一模式,而涉及母女之爱、姐妹情谊、女人间的关爱却未予以重视。它刻画的女性形象,无非是界于“天使”和“妖妇”二元对立的两极。通过对女性符号化和妖魔化,女性的真实欲望和情感受到压抑。人格发生变形,而男性统治却得以加强,从而诱使女性一步步投向男性世界。另外,女性世界的丑陋和残暴,成为将女性推向父亲世界的外在动力,其中包含着父权中心文化厌女症的隐喻。
几乎所有《灰姑娘》的结尾都是王子与灰姑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杨丽馨认为所谓永久幸福的观念,不过是父权文化的一个预谋,它切断了女性间深厚的纽带,将女性引人男性世界,变成第二性。父权机制对两性角色的界定,赋予男性第一性的特权,却把女性贬到第二性的从屑地位。这种观念不仅支配着女性,使她们自觉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男性,破坏了两性间的和谐。可见,具有代表性的三版《灰姑娘》,都体现了父权制中心文化和其企图掩盖男女不平等事实的险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