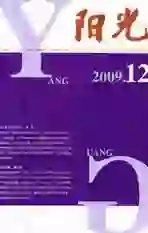彩饰背后的刀伤
2009-12-01于燕青
刀,给我的意象是搁在肉俎上和粗糙大碗烈酒旁的,是丑陋的,野性的。这更增添它令人生畏的寒光。我总也躲不过一把刀的伤害,时间之刀、命运之刀和手术室里明晃晃的刀。那些有形、无形的刀,那些冷硬、锋利的刀。
时间之刀
时间之刀是就着日光打磨,于月色里淬火的。它把我的人生轨道生生地切割成一段一段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
一个敏感的女人进入中年是痛苦的,许多中年的熟人已经离去。中年,身体的小恙像破屋顶上的窟窿,从那里望去,人生的残局依稀可见。我中年的时段特别漫长,好像总也过不完。三十岁那年,单位里一个农转非的老女人有点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于燕青你已进入中年了!”还说农村女人到这个年纪就是糟老婆子了。那意思很明显,算你中年已是沾了城市户口的光了。我第一次看见时间之刀落在我年轮上的致命纹理,听见那穿过心房纷纷凋落的细碎和凛冽,我感觉心跳的节奏明显地慢了一拍,而衰老却以刀光的速度行进着。
三十五岁那年,街上大型商场开业,小姐殷勤地向我推荐一些款式的衣服,嘴里说着:“像你这样中年的应该穿……”我又惊骇,我知道我的外表并不显老,既然还是被人轻易断定中年,那就是中年了吧。我重新翻开马尔克斯的《有人弄乱这些玫瑰》,“由于是星期天,而且雨也停了,我更想拿一束玫瑰送到我的坟上去……我独自在房间里,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我学会辨别腐烂的木头的声响,关闭的卧室里变老的空气的流动声。”感觉那就是我。那时我开始给报刊写东西,全都是中年的味道。一位诗人吃惊地问:你是提早做好进入中年的心理准备吗?我也吃惊,吃惊于他的眼神,咋没看出我积攒了三十多年的沧桑?
将奔四十五岁时,我们的中年概念忽然和国际接了轨,四十五岁才开始算中年,我的中年又得从头来过,路漫漫其修远呀。我看见掩了面的落花流水,却又阴魂不散。上聊天网站,喜欢“中年难过美人关”这个房间名。中年也能算美人?算是对我们这拨中年人一点补偿吧,以此心祭,给那些远逝的时光一次焚诗葬花般的仪式。对于衰老我是恐惧的,我没有杜拉斯那般幸运,没有年轻的男子来对我说:我更爱你的现在,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我知道她容颜的底座有神秘和成功的坚固。
可时间之刀总是那么的猝不及防,单位改制,我像一块肌体上的腐肉被一刀切处理掉了。这一刀切得我鲜血淋漓,如梦初醒。我的业余生活是一条由各种考试连接的无限延伸的隧道。我考过了中级职称,执业药师和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界内人谁都知道考执业药师难,我考过时全国还不到两万个。执业药师考场在外地,刚做完手术的我,紧张失眠,赴考场时,一件反穿的纺织线衣裹着面色蜡黄、蓬头垢面的我,偏遇最帅的男同学,捶胸顿足晚矣!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料到会和一群儿子级的学生一起考,但没想到贴着名字的考场教室门上还有出生年月,这不是让我老人家难堪?这在国外定要提抗议的吧?虽说这是自嘲调侃,个中艰辛唯有自知。我还在全国一百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数百篇的各类文章。我还有医药报的通讯员证,人事劳工和保密员的上岗证。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电脑。总之,这些年我不断给自己充电,辛勤的像只蜜蜂,到头来皆是虚空。不是说重要的岗位必须配备执业药师吗?不是说最晚在二○○四年全国药店都要配备执业药师吗?那时距二○○四年还很遥远,现在二○○四年的背影渐行渐远,而全国也只是几个大城市实行了。媒体上还在报道某某地方执业药师缺口多少多少,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执业药师像一个美丽的谎言,《中药学》《中药鉴定学》等等十几本应试书摞成高高的一堆,那些中草药一天又一天地吮吸着我生命的汁液,我单薄的影子喂养着谎言一日日进入枯萎。我的一位同事,什么软硬件也没有,她什么也不学,业余生活就是打麻将,就因为小我一岁,她留下来了。还是自嘲吧:谁叫我不晚生一年呢?来点阿Q精神吧,时间之刀切开的深渊是我肉体之身不能逾越的,那些被瓦解的、淋漓的鲜血从深渊里勃生出的只是茫然,那每一分钟的茫然都是一片不同的叶,它们不断变换着面孔,催生着命运不可预见的下一秒的表情。
那一天的阳光很明媚,我去一家药企应聘,老板居高临下的眼神轻慢地扫过我那些证,我的世界顿时下起了雪,他不屑地吐出几个字:我们需要有客户资源的业务人员。我看见那些证件在大雪之下瑟缩着身子如无家可归的乞丐,我不敢和它们埋怨的眼光对视。走过一家又一家的药店,收获的也只有白眼和冷漠。
一个中年女人走在大街上,太阳依然很亮,那些光太有杀伤力了,它其实就是时间之刀的刀刃,阻止它们如同堂吉诃德迎战风车。一个中年女人还算光鲜的衣裳里藏着一本本漂亮的证件。它们有红色的、蓝色的、咖啡色的;烫金的、绒面的、塑胶的。它们都是我的孩子,记录着我每一次分娩的苦痛,而我,却让它们苟活于这无诚的世间。我化着精致的淡妆,走在街上依然有羡慕的眼光,走进一家超市,服务员说:“哦,你的衣服真漂亮!”我惨淡地挤出明媚的笑脸。中年,虽已尘满面,鬓如霜;但也应该是成功的,踌躇满志的。我更加裹紧了我的沧桑,把它们塞进彩饰的背后。它们的呻吟,这个街道,这家商店,这些人都听不见。要躲过人们直观、简单、表面肤浅的眼睛也是容易的,我和那些外表一样光鲜的证件一同沉向时光的暗夜。
命运之刀
我的骨头和命运之刀在一场盛大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我被我的骨头绊倒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我却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的右腿膝关节又一次损伤。这是时隔七年的又一次同样的手术,那是怎样的缘分,我重返医院如同一个预先的约会,再看看那些破碎的头骨,僵硬的手臂;听听车祸和意外的故事。残弱病痛让我们惺惺相惜,医生护士都是老面孔,又像回娘家。同一条腿,不同的损伤部位。巧合、诡异,冥冥之中像有鬼神操纵。上帝若知道了,一定会对我说,那绊倒人的有罪了。上帝让我在意外中见证这个时代的病变,见证那些和我的骨头一样有罪的人和事。
终于有人把我当人才,很是雪耻。可我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激情,我已经习惯了独自蜷缩在无边的黑夜里。曾经,单位里一领导从正职降到副职,他车水马龙的办公室顿时门可罗雀。他半掩着门在里面看报纸,放报纸的休息室正通着他的办公室。他这种状况让我好生羡慕,我因此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气场。我能听见蝶翅的煽动,那是庄周化的蝶。他写过扶摇直上,高达九万里的大鹏,他最终却化作了蝶。一个灵魂的飞翔者作一只蝶足矣,孱薄的蝶翅就能煽动一场太平洋的风暴。过一种简单闲散却不颓废的生活一直是我的向往。我战胜了自己和家人的阻扰,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它其实是自己的书房,每天清茶一杯,和自己喜爱的书待着,我太需要这样一段时光,一段与嚣世拉开距离的时光,我沉迷于每一寸这样的光阴,像一株独自芬芳的植物,幸福得都有些恐惧。
好景不长,三个月后Z对我说:“大水淹到我脖子,你就帮我两个月吧!”Z是一家药企老板,他即将开业的药品批发公司急需执业药师,Z估计两个月能过行业检查。我拒绝他的坚请,可他把我当人才,那是知遇之恩,君子死知己古来便有。何况我有心太软的一面又有虚荣的一面。他开出的工资是全公司最高的,这足以让我在人前荣耀一回。回头看,我所有的不幸都和这两面有关。一个太过善良的人,自身就是地狱,虚荣又是魔鬼的诱饵。因此,我所犯的错误看似不同,其实本质相同。岂知万事易进不易出,几天后我知道两个月只是一个说梦。我渴望回归先前的生活,我是个单色调的人,注定要错过人生路上太多的色彩与斑斓。一次次的辞职不果,Z极力挽留我最后一个月。就在这最后一个月里,我倒在上班的路上,一辆运载“水玻璃”化学剂的车泄漏,“水玻璃”顾名思义就是像玻璃一样滑的水。许多摩托车滑倒,我亦在此劫中。命运是蛮横的,炒谁的鱿鱼都不须商量。我的一个踅回转身,是以这样的姿势为代价的。一切都预备好了,执业药师、老板、水玻璃、医院,像一串连环计,魔鬼躲在暗处口吐谶语,我开始了命运之刀下的呻吟。
先是索赔的艰难,那些机构都在病着,像我的腿。去公安局验伤,法医室竟设在四楼,它像一个巨人,嘲谑地看着我拖着一条伤腿艰难而上。仰视它,我心里冒出“蚯蚓、蚂蚁、屈辱”这样的词。法医说按规定我这伤要三个月后才能验,而且还要用关节镜打开关节腔察看,那等于又是一次手术,这残酷让我吃惊。法医自己也觉得这规定不妥。然而,任何不合理的东西都如同坚固的碉堡,要撼动它,必须要有董存瑞炸碉堡般的献身精神,无奈,人不是猫,听说猫有九条命。
只好违心地写下因伤势轻微自动放弃验伤。经过调解,肇事者给我两千五作为赔偿。我不情愿,调解方对我说,抓到了肇事者你们才有得赔偿,若没抓到,你们上哪索赔?不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这话乍一听有些道理,经不起细敲,显然病态语言。看来抓不到肇事者是常理,抓到了就是万幸,就该感激不尽。我后来的花费自然是这个数目的几倍。后来做手术,同病房一个和我伤情相近的打工妹伤心地说,若这份灾难可以交换,给一百万也不换。我还被告知此案将经公安部门定性为一般交通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不接受这个调解,下一步对我就更加不利。一件伤害面很广的,本应引起重视的事件,就这样大事化小了,我的一条腿也轻易地被“草菅”了。在利益面前一切情感都是脆弱的。私企无力承受我办工伤,医保不能报销,据说在家里摔伤的才能报。我不小心还把钱也丢光了,劫数连连,康复尚遥遥无期。命运的无常让我敏感而脆弱,我如成惊弓之鸟,劫灰飞尽,所有的草绳都是蛇。我看清了有形之物的脆弱,即使健康武猛的躯体也是虚空,现代工业社会,肉体怎能是机械、汽车、环境污染等杀手的对手?我常因臆想中的意外风声鹤唳,我不敢骑车了,过斑马线快要站成一尊化石。
命运之刀逼近,我只能像等待收割的麦子那样无助地迎接它的刀刃。
手术室里的刀
三个月的保守治疗失败了,只得手术。往手术室去的狭长甬道如阴阳之隔的一条河,有人渡到彼岸就回不来了。我不知道我能否回来。若把甲沟炎这样丁点大的手术也算上的话,那么有生之年我已六次搭上这渡船,我的记忆系统有很强的过滤能力,以往做过的手术已模糊,活下去需要这样的遗忘。我仰面躺在手术推床上被人推着,也许是角度和速度的变化,甬道里一些人的面容变得遥远、恍惚、不真实。我想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恐惧统摄着我。
手术是第二台,我一个人等在手术室,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我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越是延长处决的时间,越是增加对死亡的恐惧。置身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手术室,如置身旷野,孤独和恐惧在这样的空旷里疯长,此时,手术室之外的世界,有人在喝茶、喝酒、唱歌、跳舞,打球、看电视;有人笑,有人哭;有人生,有人死。一个人的快乐和苦难永远只是一个人的。天地很大,我只是一蜉蝣子,这里是生命的屋脊,也许我轻轻一跃就能出局,我出局了,世界也不会眨眨眼的。
隔壁传来金属敲击骨头的声音,我惊悚地听着,仿佛疼痛有了硬度与质感。手术室里一切都是白的,我以往的审美情趣里,白,是出尘、空灵;是好花无色、大味必淡;是蔽日的轻云、是天使的霓裳。此刻,围堵的四壁、俯视的无影灯、器皿、盖盘无不泛着白晃晃的寒光,此刻,白是如此恐怖、寒冷,是刀光钳影,血流如注的前奏。麻醉师和护士来了,我说我怕,我抓住了麻醉师的袖口好像溺水人抓住了稻草,其实只是想讨得一个安慰。人在脆弱的时候,一句温暖和安慰的话就是一剂强心剂。他忽然一声喝斥:“放手!”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同样泛着白光。看来麻药早已将这位年轻麻醉师的情感也麻醉了。我觉得我此时太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了。
进来一位漂亮的实习护士,态度也好,我像在寒冬看见春天里的花朵。我问她,别人是否也和我一样紧张恐惧?她说会的,都会的。因为别人的恐惧我反而不那么恐惧了,这似乎有点阴暗的心理,起码我觉得我不那么孤独了,也许就在隔壁,就有一个跟我一样恐惧的人,在隔壁的隔壁还有和我一样恐惧的。过去、现在、将来,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恐惧着,就像一个苦难,有很多人共同承担着。
寒光凛凛的手术刀划过我的肌肤,绽开我的白骨,我的知觉早已遁入黑夜。而此刻铺展在手术床上的我的肉体只是一个投影,我仍可看见我空出的灵魂,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灵魂是那样羸瘦和无助。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人在摇晃我,我意识到手术终于结束了。世界又亮了,又有噪杂的人声,有人在我耳边说:你听见吗?摇摇头,不然就点点头。可我的头像有千斤重不能动弹。我在医生护士的惊忧声中又过了几秒钟,我的头终于能微微地点几下,他们才放心。我拼尽吃奶的力气高喊“感谢上帝我又从彼岸渡回来了!”我还没完全从麻药里恢复,我的话像聋哑人的话,没人听得懂。
术后第一个晚上最难熬,缠着绷带的腿很疼,像是一棵枯萎的老树,上面压着冰袋,疼痛却依然将我覆盖。隔壁床是个茶农,他骑摩托车与大货车相撞,鸡蛋碰石头,当时就昏死了过去,被撞掉的牙齿散落满地,他是被医生用一根钢针插进大拇指时疼醒的,他一声尖叫把医生吓了一大跳,他从脚趾、小腿、大腿一路断上去,已经作了五次手术了,第一次手术还是在省城大医院做的,但失败了,他已经是残废了。有天夜里我听他暗自啜泣,我也不觉凄然泪下。同样的黑夜它包裹了幸福的人也包裹着悲伤的人。这个暗夜里有那么多人各自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艰难跋涉,苦难是不可比的,只有幸福才可比;幸福是鲁钝的,只有痛苦是尖锐的。痛苦是上帝高举的火炬,我不知道它能为我照亮什么。那些白天和黑夜那么的漫长,输液瓶和我的血脉嫁接了,苦涩一滴滴流进我的骨头里。
诗歌是刀尖结出的神秘的果,血一样红色的果。我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多起来,我又亲近诗歌了,我又开始写诗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为我再不能写诗。我生命最坚硬的地方麻木,愚顽,必须靠命运重锤一次次地击打,必须让一把把锋利的刀切入,我听见和骨头同等重量的东西在苏醒,我看见被乱石和荒芜遮蔽了的内心的语言,我深入我不曾抵达的纬度将它们清除。我用诗歌的刀对抗手术刀的伤害,这是最好的以牙还牙。那些文字同样迈着尖锐、疼痛蚀骨的步子,我行走的脚步立在刀尖上,这样深刻的轻盈犹如蝶在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