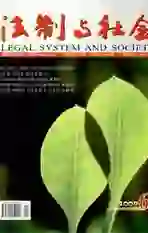略谈三鹿事件中《燕赵都市报》舆论监督报道视角的缺失
2009-07-08李云青
李云青
摘要本文以三鹿事件中《燕赵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报道为视角对舆论监督做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并就报道中舆论监督视角的缺失发表了相关见解。
关键词舆论监督报道三鹿事件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50-01
一、相关概念
在对《燕赵都市报》(以下简称《燕》)三鹿事件报道视角分析前笔者就以下概念先予以明确:
舆论监督是由监督的主体、客体、舆论等要素组成的系统。主体主要是公众。客体是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及焦点。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组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事态发展产生影响。
舆论监督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划分,根据信息公开和意见申明渠道不同,可分为社会舆论监督、组织舆论监督和媒介舆论监督。由此,媒介舆论监督只是监督形态中的一种。
在媒介舆论监督中有两个监督主体:民众和媒体。监督手段为媒体的客观报道,文字评论和漫画、调查性报道。监督的客体很多,依据汪凯在《转型中国》中的界定,主要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热点问题及相关的组织和人员,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此外,媒体在媒介舆论监督中除了监督主体,还扮演着一个信息加工者的角色。
由此,我们对《燕》对三鹿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时,可将有关因素进行定位:《燕》在该事件中所进行的是媒介舆论监督;该事件监督主体除了公众还有《燕》及其工作人员。事件中的监督客体指三鹿集团、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人员。
二、报道视角缺失的具体表现
正因为《燕》在进行监督时同时扮演监督主体和信息加工者、宣传者,才引发了它对该事件的报道方式与视角上缺失的出现。作为河北市场化的主导报纸,《燕》对该事件的报道视角选择中,过多地扮演了后者:
9月12日,报纸没有关于三鹿事件的报道。当天头版头条是襄汾溃坝事故的追踪报道。当天的《东方早报》关于三鹿事件的报道却不下二十篇,且多从公众出发。作为事件发生地的主流媒体,单纯地就其作为监督主体而言也是失职。而作为信息加工者及宣传者这一特殊的立场,则为其在该事件的后续报道中的沉默找到了理由。
13-14日,关于三鹿事件的报道主题分别是: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调查组公布三鹿问题奶粉事故情况。均为新华社通稿。14日报纸中还刊登了河北省政府的一个相关通知。这些消息中,报道视角是三鹿和政府,而它们均为监督客体。
15-24日,多是报道作为监督客体的党委、省政府及中央等对此事件的相关应对措施。事件源头三鹿集团声音很微弱,只在16日有该集团的一封道歉信,周围未配发报纸相关言论,以后也未提及。民众这一监督主体未涉及。
有趣的是,从18日开始,除了23日刊发了中共中央处理该事件的相关责任人的一条决定外,三鹿事件的相关报道从头条位置消失,此后报道零散于各版面。
三、报道视角缺失原因探析
纵观《燕》对三鹿事件报道始末,舆论监督客体的声音占绝对优势,而监督主体在报道中只零星地以“极其阳光”的面孔出现。该报作为监督主体鲜有意见表达,此事件中它主要是一个传声筒和宣传者,舆论监督的报道视角明显缺失。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体制的约束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媒体要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并对其负责。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可逾越这一体制的束缚。《燕》同样也不能逾越,尤其是作为事发当地的主要媒体。
(二)领导人的管制
某些领导由于利益牵扯、时机不对、急于掩饰等,也会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形成障碍,进而影响媒体报道视角的选择。
(三)对宣传的过度重视
作为监督主体,有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监督的权利。但其面对宣传与监督报道进行选择时,过多地将重心放在了宣传上,而作为监督主体的权利此时“退居二线”。进而,《燕》对三鹿报道视角中监督客体的绝对倾向性出现也就有了其深层原因的支撑。
(四)对舆论监督的偏颇理解
舆论监督的定义至今都没有唯一界定,但大多学者将之规定为批评和揭露报道。根据汪凯对舆论监督的界定来看,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除批评报道、揭露性报道,还有调研性报道、建议性报道。由此我们将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揭露和批评性报道,而忽略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其它层面,从而也形成了对舆论监督报道视角选择的乏力。
(五)对书面报道体裁的应用存在偏颇
该报过多地运用了消息,而忽略了其它体裁报道形式。这也是《燕》在对三鹿事件进行监督报道时出现视角错位及缺失的潜在原因。
四、相关对策探究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寻求舆论监督报道视角的灵活择取,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据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报道角度的择取。可从调研性、建议性报道的角度挖掘。
就调研性报道,纸媒,尤其是事发当地的主流报纸应重点应用。发动相关方面专家及技术人员广泛参与对事件做出规范而权威的解说,从技术、政策或其他层面找原因。一是避免流言横行,安抚民心;一是避免造成社会混乱。为提高可读性可采用互动式报道。如:刊登读者意见,让读者提问,与有关人员实现“对话”。媒体可针对事件设立专人策划小组,确立具体方案。除进行书面策划,还可由报社牵头组织社会活动面对面沟通。既可缓解公众的紧张不满情绪,也有利于政府相关工作开展。
关于建议性报道,一是可以让媒体充分发挥自身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作用,利用其握有媒体优势,对三鹿事件提出创见性建议。一是广泛刊登读者建议。这样可以在对三鹿事件的舆论监督报道视角上实现平衡,不至于出现那种政府声音一面倒现象。
二是报道体裁的选择。《燕》对三鹿事件的报道所采用的主要是消息,约占99%。只在20日和22日的时评版出现两篇评论。其他体裁报道则没有。其实,该报可充分发挥纸媒优势,充分利用除消息外的其他新闻报道。如:评论、报告文学、漫画、通讯等。多种体裁可交叉运用。这样做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政府声音、公文性通告充斥版面;一是一味迎合读者而引起负面监督效果。这就要把握好两者间的平衡,在内容上尽可能地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多提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在操作方法上也可以寓批评于表扬之中。这样以使监督客体找到平衡,打破对舆论监督的忌讳,促进监督工作的开展。舆论监督报道切忌有始无终;在报道视角上也要做好主体与客体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官腔充斥版面,舆论监督也才能切实达到应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