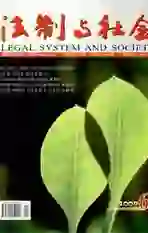论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
2009-07-08赵俊峰
赵俊峰
摘要交通事故逃逸,根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直接推定肇事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进而在刑事定罪上采用行政推定的事实,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在?本文试图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法理学角度论证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以指导和规范司法机关正确适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
关键词法律拟制行政推定刑事定罪交通肇事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84-02
一、基本案情
甲驾驶二轮摩托车,将正在道路上行走的被害人乙撞伤。肇事后,甲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救护车到来后,甲开着肇事的摩托车跟随救护车将被害人送到医院,随后既没有报警,也没有留下个人信息,即从医院逃离,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法医鉴定,乙的车祸损伤已构成重伤。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第一款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认定甲应当负全部责任。
二、争议焦点
(一)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行政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刑事定罪适用证据的可采性?
(三)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分析意见
(一)笔者认为,甲的行为应属交通肇事后逃逸,理由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院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主观上要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客观上要有逃跑行为。缺乏任何一个条件,均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交通事故逃逸。
具体而言,首先,法律追究,既包括民事责任追究,也包括行政、刑事责任追究。而抢救与听候处理是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交通肇事发生后,行为人为逃避任何一类义务,在主观上都具备了应收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都是逃避法律追究。
其次,交通肇事发生后的逃跑行为,是指在行为人人身未受到控制时,而离开的行为。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充分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这样才能对交通肇事的逃逸作出正确认定。在本案中,甲驾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虽积极抢救伤者,履行了一项基本义务,但他未履行听候处理等基本义务,就擅自离开了,即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逃跑的行为。是故,甲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笔者认为,本案中,行政推定的事实具有刑事定罪适用证据的可采性
我国将罪刑法定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定罪讲求的是排除合理怀疑,适用疑罪从无。因此,对刑事定罪采用行政推定事实是否违背这一原则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事实具有法理基础,具有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并不违背刑事立法的原则和精神。
1.实质合理性
实质理性是一种先在于、自在于法律的价值内容,立法者应当在法律规范中贯彻这种实质理性,刑事法治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实质理性的建构①。实质理性的基石则是法价值,它内在于实质理性中。根据现行法学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法律制度中有三种基本的价值:秩序、正义和个人自由②。
根据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直接推定认定行为人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进而在刑事定罪时根据此推定事实,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形以及法律规定,决定是否定罪。这种推定责任,是因为逃逸而导致无法分清肇事时的责任设定的,但无法分清责任正是因逃逸所致。逃逸者有重大过错,只能将责任推定给逃逸者。此外,如果有明确证据,证明逃逸者在肇事中无责任的,这种责任推定是可被推翻的,但至刑事诉讼中,推翻这种责任推定的证明责任在逃逸者。
应当承认,这种刑事推定责任的方式可能会侵害无辜者的合法权益,侵犯其自由权利,但从社会秩序角度而言,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用意在于督促肇事者及时救助被害人,履行法定的基本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利益,进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是一种不得已抉择。且自由永远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自由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逃逸行为应当推定为全责,因此,自由必须在这个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行使,以在最大限度的维护个人自由价值时体现法律的秩序价值。
再者,行政责任认定与刑事责任的追究,都是一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涉与剥夺。其基本法理价值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体现秩序价值,也即“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是我们现阶段法治的最大的价值目标。假如行政责任认定不适用与刑事责任追究,势必会造成,肇事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选择逃逸,破坏案发现场以逃避法律追究,这将严重影响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
2.形式合理性
陈兴良认为,法的形式主义本身意味着对满足实质理性手段的限制与约束。当法律规范确认了这种实质理性时,它就转化为形式理性。因此司法所要实现的是形式理性的坚守③。
《高院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高院解释》的规定通过“技术手段”,使本案中刑事定罪采用行政推定事实的“实质理性”具备了“形式理性”,而这一“技术手段”就是“法律拟制”。
(1)法律拟制的概念与特征
所谓法律拟制,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把一种事实当作另一种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即通过法律拟制,立法者将原本不同行为按照相同行为处理。如刑法第3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363条的规定(抢劫罪)定罪处罚。如果没有法律拟制,对上述行为显然不能以抢劫罪论处④。
法律拟制的特点在于:将原本不同的行为赋予了相同的法律效果,从而指示司法者,即使两种行为所侵犯法益不完全相同,也应依刑法相关规定作出同样的处理;法律拟制的内容必须以刑法分则相关条文的严格规定为前提,即必须做到“法有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法律拟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某种行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条件下,也必须按相关规定论处。
(2)法律拟制的原因与意义
自法律诞生至今,法律拟制一直生生不息,可以大胆预见,只要社会和法律依旧进步,拟制便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立法与司法的过程中,法律拟制依旧会保留一席之地,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法律拟制的内在原因即法律原因,以及法律拟制的外在原因即社会原因两个方面找到答案。
第一,法律拟制的内在原因,即法律原因——良法之追求。
首先,法律本身不完善需要法律拟制。法律漏洞的存在,或严格依法将导致呆板甚至不良,从而不能实现法的价值,即恶法的存在,是法律拟制的重要原因。其次,法的稳定性要求法律拟制。再次,法律职业群体特有的法律思维,需要法律拟制。具体而言,法律拟制是司法者遵循立法者的规定,其合法性要优于纯粹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法律拟制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的,适用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具有正当的形式合理性。
第二,法律拟制的外在原因,即社会原因——社会需要之满足。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⑤。即纯粹的逻辑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丰富的“常青的生活之树”,必须用“经验”来弥补缺口,而法律拟制则是经验的直接产物,是对法律漏洞的一种特殊填补方式。法律拟制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能够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综上,基于法律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说,法律拟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卡多佐指出:“由于拟制这种善意的错误,就规则和新规则之间的鸿沟常常得以跨越。在此,拟制已经不大使用了;而一旦拟制被隐藏起来,司法活动的原动力也就封闭了”⑥。
因此,我们不能用普通的刑事理论来分析其中的不足,进而指责这些条款。从法律拟制的本质来分析,既然法律已经出于某种目的进行了“拟制”,司法机关应严格遵照执行。
具体到本案,一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直接认定为全部责任,这种推定的事实属于法律拟制的事实。另一方面,《高院解释》将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且致人重伤的情形,规定为交通肇事罪。这与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罪状描述并不一致。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高院解释》的合法与合理性,实际上,《高院解释》已经通过了“法律拟制”这个手段,将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且致人重伤的情形等同于交通肇事罪处理,因为两者之间的对法益侵害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交通肇事后逃逸且致人重伤以上后果,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深,且社会危害性大,将此行为上升为犯罪予以打击,完全符合犯罪的基本理论。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立法的重复性,避免了刑法变更带来的动荡,避免了不必要的立法成本,弥补了法律漏洞。
(3)此外,刑事推定在现行立法中也有适例
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行为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情况下,推定其财产是非法财产从而构成犯罪。
综上,无论从实质合理性还是形式合理性,乃至立法适例等方面,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事实都具有理论以及现实的依据和意义。
(三)笔者认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甲在发生交通肇事后,虽然将被害人乙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其未报警、等候处理,因此,甲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第二,甲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造成被害人乙重伤的法律后果。第三,依据《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甲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第四,依据《高院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甲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五,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的事实具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应当予以确认,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推定事实的前提下,根据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应当对甲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对甲依据《高院解释》第二条定罪,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根据刑法通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同一诉讼的量刑阶段,禁止把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作为量刑要素评价,而且不得对同一量刑要素予以二次以上的刑法评价。据此,依行为所触犯的法律性质不同,处罚竞合情况下实施双重处罚尽管事实上对同一违法事实和情节进行了多次评价,但由于并非刑法上的多次评价,故与禁止重复评价不相违背⑦。
而在本案中,根据《高院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由于甲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在行政法意义上,认定为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对甲逃逸行为的第一次法律评价,但这个法律是行政法律。甲在事故中因为造成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具有逃逸情节,对此以刑事定罪。在这里对甲的逃逸行为进行了第二次法律评价,但这里的法律是刑事法律。因此,对甲的逃逸行为虽然进行了二次法律评价,但由于二次法律评价依据的法律不是同一的,故不违背刑法理论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