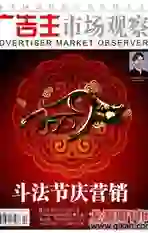刘国基:徘徊在政治与营销之间做传播
2009-06-30班允刚
班允刚

相比其他广告人,刘国基喜欢从政治角度看营销问题,对运用营销学的方法论进行政治传播充满了热情。
坐上北京地铁5号线,一路向北,在近于终点处有一座大型楼盘,即是地产广告上经常宣传的“亚北黄金地带”、“上风上水之地”——天通苑,刘国基将“书房”安于其中,他经常一个人远离喧嚣于此看书、写作、会客。满是书的房间角落里,摆挂了很多聘任证书、讲学纪念牌,从中你会看到其游走于学界、商界,来往台海两岸的多重社会身份。在不久前,刘国基即以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专家的头衔专程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做了有关“北京奥运营销”的主题演讲。
“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段表述,同样也适合与其同龄的刘国基。讲营销、论传播,侃侃而谈中,你会深刻感觉到刘国基超脱专业之上的价值关怀、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从早年在台湾组织政治运动到进入大陆置身营销传播事业,伴随他一路走来。
“左倾”斗士的不悔之路
“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过表现形式却有着个体差异,有的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试图改变现状,有的却是被动的承受者,安于在既有的秩序中挣扎。
小学时受到山东流亡老师爱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启蒙,初、高中在背地里开始大量阅读当时在台湾被划为禁书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品”,大学时通过外文期刊、大陆对外广播等各种途径了解“共产主义”,如此的成长历程,让刘国基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大陆的“精神信仰”,最终,在农村凋敝、左倾浪潮翻涌的政治、经济时代背景下,这个台湾农民的儿子走上了对既有秩序进行抗争的不悔之路。
“左倾”这一概念的含义较为复杂,因不同国家、历史时期及不同领域而不同,大致而言,其代表了一种变革、激进的价值取向。如此看来,1976年,刘国基与人组织成立的“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打出“统一祖国,在台湾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无疑是十足的政治“左倾”。正如历史上没有哪次“革命”不与牺牲相关,刘国基也因为自己的“左统”路线,被台湾“国民政府军事法庭”死刑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2年。“无所谓后悔,现在回想,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自己也只有那条路可走”,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刘国基认为,如果重新来过,他还是会继续自己的“革命”。外人认为应备感辛酸的牢狱之苦,在刘国基看来却与之前的学生生活相比改变不大,在狱中他同样天天看书, 并超越之前辅仁大学文学院法国文学系和语言学研究所的学科背景,自学了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所有课程,“监狱生活让我变成了大杂家,关得越久我的学问就越好。”他笑言。
2008年12月15日, 距1949年,60载,距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已30春秋,两岸 “三通”历尽波折,终于实现,“我们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刘国基的高兴溢于言表。
政治与营销,在刘国基的职业历程中是合乎逻辑的统一体,“虽然本来并非立志要做广告人,但冥冥之中总觉得好像有种力量在推动自己朝这个方向走来”。从在“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团体里管理宣传工作,撒传单、组织集会、与各派群众辩论,到出狱后创办《海峡评论》杂志,于1996年、1999年协助林洋港、李敖竞选“台湾总统”,以及在1995~1996年蜂起的“台湾地下广播电台运动”中,他还担任过“call-in”节目主持人,是个让台独人士头痛的广播名嘴,“刘氏脱口秀”在当时拥有包括“前国民政府高层军政界人物”如郝柏村、缪伦等在内的大量忠实听众,刘国基认为上述所有“传播实战”的历练,都为其日后从事营销传播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87年7月14日,恰巧与历史上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同天,国民党解除了台湾的戒严令,刘国基也提前结束了牢狱生活,在母亲已病逝7日后回到台中乡下老家。人事全非、举目悲凉,在处理完老母丧事后刘国基又毅然北上,接任夏潮联谊会主任秘书一职,并于1988年4月成为“反独促统”政治团体 ——“中国统一联盟”的建盟第一秘书长。同年,7月14日,刘国基也开始了与祖国大陆的真正实际接触,莆田、湄洲岛、妈祖庙,漳州、泉州、海南岛,北京、上海、广州,通过父祖之乡以及大陆核心城市之旅,一直属于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天堂”概念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虽然有差距但却是真实、亲切的。此后多年中,刘国基以政治团体成员、商人、新闻记者等多种身份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但大多只是事务性、短暂的停留,如此,接触越多,知道得却越少,从而其也便有了深入了解大陆的渴望。
1989年冬季,在台湾南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国际部总经理的刘国基,被派往马尼拉工作,主要负责针对菲律宾政府与国会的“府会公关”业务。经过东南亚各国的巡回工作,刘国基加深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阶段的理解,也坚定了对祖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宏观成就的肯定认识。1992年春天,他回到台北担任《海峡评论》主编,并于同年夏考入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接受专业的新闻记者训练并研究“新形势”下台湾大学校园的政治生态。1994年6月,刘国基获得台湾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之后便进入台湾知名杂志《远见》。1995年,在《远见》杂志担任高级编辑的刘国基通过“新台湾人”专题获得了台湾最高杂志新闻报道奖——金鼎奖,不过,这样的成绩为其带来的却不是应有的回报,而是由台湾特务系统以行政权力授意下的排挤。
无奈、愤懑之下,加之为了进一步了解大陆,刘国基于199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盛世长城担任公关总监,开始常住大陆,并正式进入营销传播行业。不过,虽然置身领域已经发生变化,但开创性的“左倾”举动却没有在刘国基身上消失。
“营销先行者”的大陆13年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媒体对商业化运作的认识极为陌生,陷入本身发展的桎梏而并不自知。1997年,应客户中国宝洁提议,时任实力媒体公关总监的刘国基组织了中国电视媒体30人考察团(囊括全国省级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或主管经营的副台长)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考察CBS 、NBC、ABC、CNN、FOX等商业电视台的广告运作模式,了解纽约Zenith Media和A.C.Nielson的作业方法,以及参观可口可乐、宝洁公司总部,了解其广告媒介策划、媒介购买专业流程和媒介关系维护模式,这可谓是对中国电视广告经营思想的一次重要启蒙行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针对中国电视台没有广告监测手段、缺乏商业广告运营思路的现状,从美国回来后,刘国基趁热打铁,开始组织电视收视率研讨会,从收视率调查的基本概念和国家网、省级网、城市网不同抽样母体的差异,以及电视收视率调查方法论的介绍,到对如何将收视率运用于广告定价、节目编排、媒介策划的讲解,为中国电视媒介从懵懂中快速成长扎实地施了一次底肥。当时由刘国基倡导印发的实力媒体——《新闻通讯》,更是成了抢手的资料,这本印制粗糙的小刊物对在中国普及媒体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无论对于政治或经济领域,打破、开创的举动永远与风险相伴,刘国基在营销传播的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2001年,作为创办人、CEO的刘国基离开主政3年的中华传媒网,虽然这一传媒领域的网络资讯平台在当时已建立起了很强的影响力,“是我无能,没有找准盈利模式,知识分子不可尸位素餐……”这是他离开时的无奈慨叹。不过,直到今天,刘国基认为:纯粹从商业模式上来看,中华传媒网以建立透明、直接、高速、互动、一站式的线上媒介广告交易平台为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太过早熟,广告主、媒体都不热衷,“触及了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利益既得者,即使今天来做也成功不了。”离开中华传媒网,刘国基短暂地担任了海润国际广告公司执行总裁后便前往长沙,成为中联重工科技公司主管品牌的策划总裁,“为一个重工业企业负责品牌整合工作,与广告界熟悉的快销品经验完全不同,很有意思!尤其在股票上市的大型国企领导阶层工作,真是妙不可言……”他含糊地将这段经历轻轻带过。
截止到目前,刘国基在大陆从事营销传播已13年,在广告公司、媒体、企业都担任过重要职务,服务的知名品牌有中国宝洁、西安杨森制药、诺基亚、重庆奥妮集团、北京现代汽车、东风雪铁龙、中联重科、五粮液、衡水老白干等等……同时他也做过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湖南电广传媒集团、重庆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广告经营策略顾问,不过,因为在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的多年教书经历,及担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广告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商务品牌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大学媒介与市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等多项职务的缘故,刘国基给人更多的是一个学者形象,他也坦言:“我还不是一个经济动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从事营销工作的同时,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台湾的关心、对两岸政治的关注,而且其自认在营销理论的阐述中更具有“政治高度”。
刘老师的“政治营销课”
“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据说这是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时任宣传部长、知名广告人艾尔伯特·拉斯克尔所说的一句话,其日后成了广告人们用来引以为荣的名言。不论罗斯福的意欲为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政治确实需要营销,营销同样也要关涉政治,不过对于“政治营销”的认识与研究,中国大陆显然是与美国、台湾有差距的,这也是刘国基一直想在内地高校开始此门课程的原因。
在台湾开展政治运动时的刘国基被称为“左”,是因为其在台湾主张民族统一、社会主义,与时局所倡相背。如今,在课堂上宣扬爱国主义与民族理想却被学生称为“左”,刘老师为之有些不解!
经历过人生的困苦、体味过缺乏强大祖国依靠的悲伤、感受到了中国未来的大好形势,刘国基在课堂上经常为学生讲解“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改革开放难遇、盛世可期”的道理。不过,作为营销传播领域的专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虽然生产力强大,但缺少世界级的民族品牌,而这同样是其要给学生做精神建设、开展政治营销的原因。在刘国基看来,当技术、创新问题被逐渐解决后,一流的产品能否跃升为一流的品牌,与本国人民是否拥有“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onsumer Ethnocentrism)”密切相关。同时,他认为,消费者的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是经由“品牌洗脑”、慢慢培养而成的,需要政府、企业、学术、广告各界来共同努力。“因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自鸦片战争失落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才算恢复,以此为基础,中国人在获得底气后,中国元素、中国概念才能被接受,中国制造才有希望,最终才能成就民族自主品牌的溢价。”他说。
在实力媒体做过媒介策划总监、在昌荣传媒担任过副总裁的刘国基,对中国媒介运营领域同样充满着鲜明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期待,“中国本土媒介购买公司的优势不在购买,而在销售,通过成为媒体广告资源销售总代理,构筑‘本土媒介销售的卡特尔来与‘外资的媒介购买卡特尔进行对抗,才有希望。”他认为这是其对中国本土广告未来的鼓励!
对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心态的培育充满自信,对中国本土广告行业的发展怀有期待,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位整合营销传播博士,刘国基在对发轫于20 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应用前景的认识上,显然没有美国西北大学唐·舒尔兹博士那样乐观,当然也不会跟随其一同喊出“现在是传播学全面接管营销学的时代”。“不要说企业,即使是广告公司对整合营销传播也不认识。”在刘国基看来,目前做得比较多的只是整合传播,而真正的整合营销传播涉及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垂直整合、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水平整合、内外合作关系的整合以及财务整合等,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现实中,企业也不会给予营销执行者那么大的权力,理论很好讲,实际操作却很难。在中国,企业老板越开明,认识越到位,品牌整合做得就会越好。”
说话喜欢直来直去的刘国基,在刚结束不久的一次有关“电视覆盖率”的研讨会上,明知会令一些人不快,其还是说了一番泼冷水的实话。在海峡两岸都得罪过人,不过为人坦诚,力求与人为善的刘国基更结交了很多朋友。回顾这些年所走过的历程,之于广告领域,他认为自己始终在传道、授业、解惑,一直在做整合营销传播的布道者,唤醒中国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帮助中国企业打造民族自主品牌,期冀全世界都认可中国制造的品牌;之于政治,他坦言至今也不知自己到底是否对其怀有兴趣,只是内心一直存有“救国救民”的价值追求,“本性做不了政客,也许只是对政治的批评有兴趣而已”。相比其他广告人,刘国基喜欢从政治角度看营销问题,对运用营销学的方法论进行政治传播充满了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