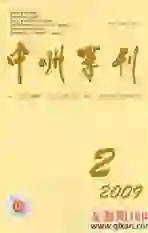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2009-04-14张乐林
张乐林
摘要: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韦小宝;解构;建构;侠义;真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18-03
一
《鹿鼎记》不仅在金庸的武侠作品中,即使放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中看都是相当另类的作品。作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骨碌碌转着一双贼眼珠的韦小宝,跻身在顶天立地豪气干云重义轻生至情至性的萧峰杨过令狐冲郭靖等一干“侠之大者”中,一种意味深长的反讽也就油然而生。于是,有人说《鹿鼎记》是反武侠之作,也有人说它更接近历史小说,但也有人说《鹿鼎记》:“站在俯视历史和世俗的思想高度上,探询着扩拓着侠义的真内涵和真精神。”
这些说法的产生,都有着立足于小说文本的依据。虽然结论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鹿鼎记》的小说文本在结构过程中,显然创造出了产生诸多阐释可能的空间。作者金庸是这样说的:“《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金庸以他强大的远远超出一般武侠小说作者的认识能力和对人性的关怀,成功地将武侠小说这一通俗小说形式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他在对武侠小说固有的程式化表达形式充分继承的基础上,以丰沛的想像力、诗化和象征性的表达形式、以及巨大的情感蕴藉,革命性地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调与内涵。“射雕三部曲”可视为标志,其后在《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造就了“射雕三部曲”成功的元素得到了更加纯熟更加充分的利用。可以说在《鹿鼎记》之前的金庸,已经掌握了武侠小说创作独到的法门,将功力练到了独步一时的境界,但在《鹿鼎记》中,金庸所尝试的“新”的创造近乎经脉逆行,他颠覆性的舍弃了此前所有的使他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形式性元素,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带有相当程度否定性的形式。完成了这部风格迥异的作品。《鹿鼎记》的接受过程也说明了金庸的创造,已经新到了“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的程度。
作为金庸创新尝试集中体现的韦小宝这一形象,从形式上看的确可以说是对以前金庸笔下塑造的侠的形象的全面反动。作者用一个市井小流氓的形象替代了纵横天地间的大英雄来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这个尝试本身,表明了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武侠小说——包括经由他自己改革创新后的新派武侠小说——既有的为他提供的表达认识的程式化的形式,他甚至以一种粉碎既有形式的形式来结构武侠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鹿鼎记》的确含有解构性的因素。但《鹿鼎记》对武侠小说表达形式上的解构,并不构成对武侠小说本身的解构。《鹿鼎记》之于武侠小说,与《唐。吉可德》之于骑士小说不同,后者包含着对没落僵化的骑士小说本身的批判和否定,而金庸在《鹿鼎记》中实现的创新,为武侠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韦小宝形象的塑造,也是金庸探讨侠义精神内涵的一种新形式或者一个新角度,作者在解构中时刻又在建构。
二
首先,金庸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
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血缘和师门对于侠是具有神圣性的,背负血海深仇是很多大侠成长的重要心理背景,所投师门又是大侠成长的重要精神背景,而师门的荣辱兴衰更是大侠义不容辞的担当。虽然在以往的作品中,血缘和师门对于人物的影响力量,金庸的表现并不是单项度的,他以充满张力的故事建构表现了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比如血缘之于杨康,继而之于杨过,师门之与令狐冲。但血缘和师门的神圣性从来不曾遭到过作者的否定,即使这种神圣性成为悲剧的根源,比如血缘之于萧峰,师门之于杨过。作者通过悲剧本身提出的质疑更加凸现了血缘和师门的神圣性。特别是在《神雕侠侣》中,金庸以充满实验精神的故事建构,挑战了人们对固有的师徒关系的认识,但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这种挑战并没有突破接受的底线,杨过精神成长的真正师傅是郭靖,而不是小龙女。
但在《鹿鼎记》中,金庸通过对韦小宝形象的塑造,对血缘和师门的神圣性做了彻底解构。首先是韦小宝的身世,作为妓院皮肉生涯的意外,韦小宝在父系血缘上陷入了一种完全无从追索的境况。无从追索也无意追索,极端不正常的成长环境,使韦小宝完全没有血缘上的神圣感,他以一种更为粗糙随便、更为实用的态度,对待血缘这一相对虚无的概念。逢到危机关头,可以拿自己的祖宗父母发誓,对母亲的皮肉生涯也安之若素,顶多是在心里骂嫖客两句瘟生王八之类的脏话,对母亲却能很“客观”的批评她作婊子也不用心,不肯多学几只曲子。至于师门,大概找不到比韦小宝更不敬师门的弟子了。对于几个师父,陈近南、康熙、九难、洪岛主,韦小宝极尽阳奉阴违之能事。武侠小说主人公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师承武功的精进程度,而且在金庸以往作品中,武功的精进程度往往于主人公的精神成长高度既有象征性的关系,也有实际的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联系,同时武功这一表现形式还意味着忠诚和担当。但韦小宝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有幸得当时几位绝顶高手为师,却除了脱身用的救急招数之外,他一点都不肯多学。依赖“市井三招”和“韦氏三宝”,却也有惊无险地在江湖和宫廷间闯荡,甚至用“市井三招”中的洒石灰一招救了师傅陈近南。
这种解构性的设置,其实是在为建构侠义精神的影响力做的铺垫,也就是所谓的“背面傅粉”。作者建构性的叙述是通过陈近南与韦小宝的师徒关系的设置来完成的。在韦小宝的诸多师父中,陈近南是他从内心唯一真正作为师父来接受和认可的。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陈近南的形象,却是我们在金庸其他作品中所熟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化身,“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金庸让韦小宝“幸运”地被这样一位大侠收为弟子,韦小宝从书场戏台上得来的一点关于侠义的种子,就有了持续成长的光源和水源。陈近南对于韦小宝的影响,却又始终被作者以相聚短暂的方式控制为一种熏陶和笼罩,这是一种有距离的影响。因为有距离,就有效地规避了陈近南的行为方式在韦小宝世界中的具体化,作为一个少年,小宝如果跟在陈近南的身边,恐怕行为方式会得到相当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一个”的韦小宝了。同样因为有距离,韦小宝对侠义精神的领会,因为不具体而显得混沌却境界更为开阔。
虽然有距离,以陈近南为象征的侠义精神对韦小宝是有
巨大控制力的,这使得韦小宝每每到了关键时刻,能够放弃通常的实用主义原则,以侠的担当和勇气,甘冒奇险去救朋友,又因为韦小宝的侠义是混沌开阔的,所以他的勇气和担当是针对所有朋友的,无论是康熙还是天地会,韦小宝适用同样原则。
于是,通过韦小宝这一形象,金庸继续了他在以前作品中对具有理想价值的侠义精神的肯定,从小说修辞的角度来说,一个侠肝义胆英雄的舍生取义,反而不如一个常常见利忘义苟且实际的小痞子,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更加能凸现侠义精神的力量。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一形象,让侠义精神从江湖照耀进了市井,让侠的概念从虚幻落到了现实,让充满弱点的普通人获得了实践“侠义”的可能性。韦小宝的形象还让金庸获得了一个更方便的角度,继续他在其他作品中已有的探讨,面对一个具体的生命和面对一个抽象的概念,“侠义”带给主人公的矛盾和困惑。
三
其次,金庸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我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中,包括《鹿鼎记》此前金庸的作品,主人公或者较为重要的人物,其行动的驱动力都带有某种崇高感,比如复仇、报国、拯救天下苍生,即使是为了爱情,同样也具有较高的精神指向。但韦小宝的行动驱动力却被金庸设计为财和色,这样设计的解构性毋庸多言。与此同时,金庸的建构是通过在韦小宝的形象中植入感情这一重要因素来实现的。在对人性充分理解的前提下,金庸选择了感情这个合理的却又强大的完全能与财色相抗衡的力量。对真挚感情的重视和珍惜,被金庸设计为韦小宝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
财与色是重要的人生资源,这是韦小宝从妓院这个他人生第一所学校中学到的重要经验,而他对世界的认识几乎也完全遵循着“妓院模式”。无论朝廷官场还是江湖中的帮派,就是到了罗刹国,也充满了虚与委蛇阿谀奉承出卖交换欺诈背叛,处处都是不择手段欲壑难填的贪婪,严酷点儿说社会完全如同一座放大的“妓院”,所以韦小宝的“妓院经验”出了鸣玉坊也放之四海而皆准。韦小宝歪打正着一路通吃,捞得盆满钵满不亦乐乎。与“妓院经验”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堕落,却并没有真的降临到韦小宝身上,这是因为金庸为这一形象设计了具有拯救意味的双翼,一翼是前文所说的侠义精神。另一翼则是真情。这双翼相辅相成,带着韦小宝的人格飞离了堕落的泥沼,使痞气和流氓气最终成为韦小宝这一形象的表象,而其精神内涵却闪耀着对侠义和真情的真实渴望的光芒。
这样的设计也是符合人性实际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为此设计提供注脚。对韦小宝的心理成长过程稍做推断就能发现,人与人之间健康的真挚的情感与关怀的缺失,使他天然形成了对真情的敏感。所以小玄子的友谊与陈近南的温暖,以及像与茅十八这样的江湖朋友的性情之交,甚至陶宫娥跟他的亲近,都让他十分珍惜,这些真情对韦小宝的意义远远大过荣华富贵。“妓院经验”带来的重要原则是快乐,妓院本身就是一个追欢买笑的地方,快乐是这里至高无上的原则,韦小宝的基调是快乐的。就是暂时被人欺负了,韦小宝也有精神胜利的方法使自己立刻快乐起来。他的烦恼、痛苦和挣扎基本上都是侠义和真情带给他的。可是一旦情势需要他必须做出取舍时,韦小宝的选择就不再遵循趋利避害的快乐原则了,金庸总让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侠义,选择了真情。
当他决定冒着被灭口的危险向康熙吐露太后寝宫的秘密时,他:“握住了康熙的手,颤声道:‘小玄子,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行吗?”接下去,他说:“有一件机密大事,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说,可是不能跟我主子万岁爷说。皇上听了要砍我的脑袋,小玄子当我是朋友,或者不要紧。”
而面对师父陈近南的死,金庸一反惯用的谐谑的笔调。而是用诗化的大抒情的笔调描写了此时韦小宝的痛苦:“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成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陷,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另一段描写韦小宝情感世界的重要文字是三十九回“扬州探母”,这段文字谐谑其表,悲酸其里,韦春芳自顾自哭着笑着,心疼新缎子衣裳而生气打儿子耳光又替儿子偷火腿,韦小宝唯一能让母亲相信的发财理由是掷骰子,母子越闹越滑稽,而读来总有一种难言的沉重。韦小宝似乎对这沉重并不是全无感觉,但他以对母亲的体恤与理解,最后用一把举重若轻的“满堂红”笑对这个荒诞残酷的世界了。
对于韦小宝异常丰富的爱情生活,金庸首先也是解构性的设计,以俗气和流氓气以及对象泛滥的迷恋,消解了“神雕侠侣”式爱情的诗性与忠贞,韦小宝以“十八摸”为主题曲的爱情大合唱,对于通常的爱情审美心理无异是一大挑战。但是金庸通过对韦小宝情敌的塑造,那几个江湖少侠公侯贵胄包括称霸一方的江湖头领,其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孱弱、猥琐、虚伪甚至畸形,反衬出韦小宝情感的健康与真诚,尤其在以侠义和真情为标尺的比较中,韦小宝的情敌都败在了他的手下。也就是说,每个女子在自己有限的选择中,依然还是选择了侠义和真情。
四
在《鹿鼎记》对韦小宝形象的塑造中,金庸以“解构中建构”的方式贯彻了他“重义崇情”的立场。而这两点,是“侠”这个大概念中至关重要的两个维度。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金庸超越前辈和同行的地方,是把“侠”放在“人”的大前提下进行塑造的。不仅是在《鹿鼎记》中,早在他创作“射雕三部曲”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在对读者传达一个模式化符号化的侠义概念,他的故事几乎对所有通常武侠故事中天经地义的关系和概念,都放在了“人”的背景下提出了质疑和讨论,譬如正与邪的复杂性,侠义与生命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形象把这种质疑和讨论推向了新的深度。金庸显然是一个有着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鹿鼎记》虽然是到现在为止的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但它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对其后武侠创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日加彰显。
责任编辑: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