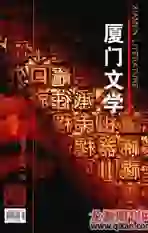福建诗歌链(一)
2009-02-10陈仲义
陈仲义
一 独立、自由的心灵律令
———读蔡其矫“波浪”
与大多数从延安出来的“老三八”不同,蔡其矫在同辈中很另类,他一向我行我素,被称为诗坛“独行侠”。他似乎对周遭的环境“一无所知”:不知屈膝、媚世,少有伪装、逃避,总以赤子之心面对世势人生。1958年全民大跃进,他视若无人,写出离经叛道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几遭灭顶,同年在报纸公开喊出:“青春万岁、月亮万岁、少女万岁”。1962年举国沉闷,噤若寒蝉,他不合时宜唱出《波浪》,严重触犯天条。他遵循的是,心灵世界的自由律令。
《波浪》是大陆冰封时期难得的抗寒品种,也是蔡老自己心仪的作品,每每用来做朗诵会压轴。我曾三次聆听他的朗诵。最后一次是在他逝世前半年(时值89岁高龄)。大红唐装,卷曲飘洒的银发,像波涛抖动的手势,浓重的闽南地瓜腔,因激情澎湃反而叫听众深受感染。
此诗以波浪作为动力牵引,层层推进;同时也把波浪作为自我意志的写照,它忠于自我意识、自我感觉,把威权主义不放在眼里,挑衅专制,反对独霸,深信人民的力量。
“永无止息地运动”是波浪存在的形态,而这一形态赋予波浪无穷的活力与生气。它提挈式的包容波浪的广阔性格、气质,以及波浪的本质力量。前四节主要写波浪的丰富、热情、和爱心,我们应该把它看做是诗人神志情怀的寄托。其间波浪对船只抚爱,照耀,陪伴,走遍天涯海角,成为“航海者亲密的伙伴”,是由衷的对美好事物的肯定和赞美,情真意切。“那时你的呼吸比玫瑰还要温柔迷人”,诗人一直把波浪当女性、当情人来写,显示了大海温柔的一面。
后半部分五到七节,则笔锋一抖,写出波浪凶猛狰狞的另一侧面“你掀起严峻的山峰”,借此质问强权政治:
是因为你厌恶灾难吗?
是因为你憎恨强权吗?
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
这样的“狗胆包天”,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出自天性,诗人对心灵自由无限向往,对压抑、窒息人性势力的抗争,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桎梏的。因为,无论从天性上说或从现代法理上讲,它(他)是“不能忍受强暴的呼喝”,“更不能服从邪道的压制”。波浪(水的代表),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这是一个万古有效的法则。如果你硬要在人民的头上建立统治,那么人民将用全力把你打倒。诗人的警告,在当时真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对着铡刀。
最后一段则表明了诗人处世的鲜明态度,对百姓大众、弱小群体亲和关爱,对强权暴力进行阻止。如今这两句简单有力的诗句,“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以它巨大的人民性,镌刻在紫帽山下,圆板村蔡老的墓碑上,成为朴素的箴言,继续被瞻仰他拥戴他的人们默默传诵。
本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一格,全诗中四个“波浪啊”组成回荡的旋律,最后推向高潮,给人荡气回肠的鼓舞。波浪刚柔相济的组合,赋以波浪多姿多彩的丰富内涵。
这位海的子民,终生与波浪为伍:猛烈扑打灾难和阴影/把暴力撕成碎片/以浅蓝的波浪/张起正义的弦琴/永远用胜利者的眼睛/至高无上的欢乐/冲破一切界限/跳动着万古自由的心。
独立、自由不羁的意志,是诗人的试金石。
附
波 浪
蔡其矫
永无止息地运动,
应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
一切都因你而生动,
波浪啊!
没有你,天空和大海多么单调,
没有你,海上的道路就可怕地寂寞;
你是航海者最亲密的伙伴,
波浪啊!
你抚爱船只,照耀白帆,
飞溅的水花是你露出雪白的牙齿
微笑着,伴随船上的水手
走遍天涯海角。
今天,我以欢乐的心回忆
当你镜子般发着柔光,
让天空的彩霞舞衣飘动,
那时你的呼吸比玫瑰还要温柔迷人。
可是,为什么,当风暴来到,
你的心是多么不平静,
你掀起严峻的山峰
却比暴风还要凶猛?
是因为你厌恶灾难吗?
是因为你憎恨强权吗?
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
我也不能忍受强暴的呼喝,
更不能服从邪道的压制;
我多么羡慕你的性子
波浪啊!
对水藻是细语,
对巨风是抗争,
生活正应像你这样爱憎分明
波———浪———啊!
蔡其矫,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省晋江县园坂村。幼年侨居印尼泗水。1936年在上海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8年投奔延安。早年诗作结为《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中期有《蔡其矫诗选》,后有《蔡其矫诗歌回廊》共8集等。
二 异化,连同“存在性不安”
———读舒婷“流水线”
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来,揉着发悃的眼皮、满脑子迷迷糊糊;抬头,夜空的星星晕头转向;闭眼,无数飞舞的焊点火冒金花。星星、焊点、金花,三种意象相互缠绕、叠加,构成那个夜晚的某种契机。原先,宇宙中那么生动的星相,此时由于疲惫“移情”,也变得“麻木”了;本来,大自然那么多活泼的小树,也在流水线的固定“排序”下,变得机械呆板了。女诗人凭着敏锐直觉,从多年生存体验里,拽住了一个“诗想”。
1972年底,女诗人从插队的地方调回城里,先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处在生产第一线经常“三班倒”,因此对流水线“情有独钟”。8年积劳,“忽然”发作于那个夜晚。
第一段写四种流水线(时间的、空间的、工作的、自然的),为其后的思绪“提升”做了感性铺垫。第二段引出流水线运行轨迹———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生的———所造成的弊端病态。诗人身在其中,凭着与对象“一种共同的节拍”,意识到这种陷阱的可怕、可虑。第三段写处于这种包围圈里,诗人终于醒悟,外力无休止的运转,势必荑平人的感性棱角,约束人的自由空间。人在机械的轨道里,自我最容易被剥夺篡改,人的“自在”,早被先天“异在”了,何谈还有什么能力“自为”呢?人一旦落入“异在”力量的同化主宰中,主体性丧失殆尽,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以流水线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不断高歌猛进,但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难免叫人沦为流水线的某种工序。尤其是密集型手工操作,在“驯服工具论”支配下,掩盖了广大低层员工的劳动辛酸;遮蔽了活生生的具体个人,严重扭曲了人性;严密组织的机器和教条模式运转,从物质到精神,都教人陷入统一的铁律里。
“异化”问题,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可是27年前,是大大的雷区!揭示流水线造成的异化,可说是该诗的表层宗旨,但在当年却有点“石破天惊”。因为当时整个主流社会都不敢承认有任何“异化”。女诗人以亲身的切肤之痛说出了它的“真谛”:人以自身的精明与精密,制造了流水线,反过来,精密的流水线奴役了人的灵性:人受惠于工业文明种种好处,反过来,人自身也被不断规则化,这是无法逃避的悖论。
此诗的价值,我以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前卫地把多年来,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给率先戳破了:让长期来,人们因高度组织化、律令化的麻痹神经,有了些许激动,并引发相关问题的反思:包括越来越来突出的权利异化(权利出租经由利润获取改变原来性质)、技术异化(武装到牙齿的工具理性把人变为零件)、文明异化(其负面导致一系列非人性戕害),如此等等,这些联想的“启蒙”,就是该诗产出的最大社会效果。
现在,我倒觉得,该诗的冲击性,还不在异化层面,而是最后一节:“或者由于习惯/或者由于悲哀/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也没有力量关怀”。这种出自直接体验的哀叹,不应该看成是简单的宿命感伤,而是作者直击人———作为存在物的本源性思考。
当代存在论心理学家和文化批判家莱思,在研究众多精神病理后,提出“存在性不安”命题。笔者以为,借用这一说法,完全可以将其引申为人的一种基本生存境遇。人,无时不面临着“存在性不安”,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摆脱“死亡逼近”的,而在当下的生存链条中,同样难以祛除各种焦虑:比如吞没焦虑、爆聚焦虑、僵化焦虑、异化焦虑。这些焦虑,使个体僵死而不生动,被动而缺乏自主,以及非人化征候,被异在力量吞没……等等,我们在该诗的末尾,闻到了浓浓的“存在性不安”的气味。
如果我们认可“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一种基本景况,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流水线》“悲观绝望”(80年代清污运动,该诗与《彗星》等被红头文件列为毒草)。这对于向来过于乐观、缺乏悲剧情怀的国人来说,它的出现,恰恰是一种久违了的提醒。因为对于人的“关怀”,始终应是第一位的和“终极”性的。
附
流水线
舒 婷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星星一定疲倦了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
小树都病了
烟尘和单调使它们
失去了线条和色彩
一切我都感觉到了
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但是奇怪
我惟独不能感觉到
我自己的存在
仿佛丛树与星群
或者由于习惯
或者由于悲哀
对本身已成的定局
再也没有力量关怀
1980.1-2
舒 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厦门人。1969年下乡插队开始写作。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舒婷的诗》等,境外出版5个语种9种个人诗译本。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