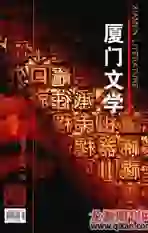晋江杂忆
2009-02-10王炳根
王炳根
晋江在我的生命中,不下于我的故乡。故乡生我养我,晋江养我育我,这里有我的爱,我的欢乐,我的生命印记,我无数的沙地上的脚印。
此刻,根叶绿营庭院,正下着不尽的夏季雨,我在书桌前回忆晋江,犹如回到我湿漉漉的故乡。
沙土地上的印痕
我的故乡江西进贤,那是一片红色土地,每当下雨之时,便是满地泥泞,晋江的沙土地,让我感受到了雨后的清爽。1969年12月24日,我在并不寒冷的冬雨中,从解放牌军用卡车上跳下,落在了晋江的沙土地上,第一感觉便是雨后的清爽。
六七十年代的晋江与今日之晋江,不可同日而语。清爽的沙土地却是贫瘠的,贫瘠到比我的故乡还要艰苦。适宜于沙土地生长的地瓜,是普通百姓的主粮,从新鲜的地瓜到地瓜干到地瓜米,一路吃去,四季循环,我的故乡再贫困,也是一天有三餐米饭可食。福建的部队却又另当别论,白米、面粉与黄豆均为主食,独是没有地瓜,这让“福建兵”很有一些不习惯,有时望着地瓜地,思念着地瓜,这种对地瓜的特殊感情,招致了“地瓜兵”、“老地瓜”之类的绰号。
晋江的沙土地适于种地瓜,却是不宜种树,江西老家的大樟树、柳树甚至苦楝树,这里都看不见,比较容易生长的是相思树、木麻黄与小叶桉,就是这些树,也大都生长在军营的四周,所以,你只要看见哪一处树木丛生,那儿便是军营。那时晋江是前线,军营很多,尤其是山间与海滨,往往驻扎着部队。军营周边的百姓,望着那片绿色的营地,既有一种神秘感,也有几分羡慕之情或嫉妒之心,勇敢一点的“查某”(闽南语,意为女人),则背着箩筐,带上竹耙与铁线,绕过军营的岗哨,进入营区,用竹耙耙着落在沙地上木麻黄的针叶,用铁线穿着小叶桉的宽叶,装满箩筐,悄悄溜走,回到家那可是上等的燃料。如果此时遇上哨兵或者哨兵听见动静而赶来,便会有些麻烦,因为,驻扎在福建前线的军营,敌情观念很强,不允许除军人之外的任何人随便出入,就是驻地的“查某”捡拾树叶也是违规的,驱赶“查某”便成了哨兵的一项任务,有时“查某”从林间树下惶惶而逃,全然顾不得刚刚捡拾入筐,现又抖落在地的树叶了。
“打捕”(闽南语,意为男人)进入军营,则是另外的一种方式。晋江的土地多沙,山上则多石,石是晋江的重要建筑材料。可能因为抗台风的关系吧,那时晋江许多的房屋,包括一些军营都用石头建成,石墙、石窗、石门框、石屋顶。这里所说的石头就是现在称之为花岗岩的石头,那时没有切片机与磨光机,全靠一支钢钎一把铁锤,加上“打捕”的一双手,从山上的巨岩峭壁上开采下来,形成的条石与板石需要运下山去,也没有起重机,全靠一条粗麻绳,一根木撬棍,将其装上板车,板车下山,没有公路,陡峭的山道上,搬运者不是推车,而是用肩扛住顶着板车上的挡木,阻止板车下行的速度,人工的阻止与自然的下滑力在山道上较量、搏斗,给沙石的土地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辙痕。这道深深的车辙之印,若是从军营之中划过,岗哨也得让路,士兵操练场也要允许通过。那运载着沉重石条的木板车,那赤膊弯腰的汗流满面的“打捕”,便是晋江沙土地上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不得靠近!
福埔车站
现在晋江的交通真是四通八达,就是村镇之间的公路也是水泥路面四个车道,且有绿化带。2004年我在晋江博物馆举办“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站在新建的世纪大道上,望着我曾在那儿服役多年的罗裳山,宽阔的大道从师部门前切过,罗裳山至青阳镇,仿佛一脚油门便可到达,可是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却是很遥远的哟。
驻扎在罗裳山的部队,一般外界称其为“罗山师部”,代号为6735部队,番号则是守备第三师,之前称为八师,之后是十三师。全师守卫的海岸线很长,从惠安的金峰到金井的围头,分布驻扎着这个师的连队。我那时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报道员,经常要到连队去采访。虽然军队许多的事情都是自成一体的,但是交通没有体系,几部北京吉普车,一个小车班,那是专门为师首长服务的,若跟随其后下部队,则可享受北京吉普的待遇,多数的情况下,是自己一个人打了背包下连队。如果是去石狮、永宁、金井的方向还好,如果去惠安方向,那可就麻烦得多了。
无论往哪一个方向,位于罗裳山脚下的福埔车站,是师部人员搭乘公共汽车惟一的通道。所谓福埔车站,就是一间大概只有十来个平方米、处于青阳、石狮与安海交接点上的石砌平房,石门、石扇,里面空落,没有座椅,没有售票窗口,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身上背了一只装有通往各地车票的帆布包。福埔车站从不发车,只接过路车,天知道哪一班车会在这个小小的车站停下?所以,只有在车到站停稳后,售票人员才站在车门前售票,如果不停,他便退到屋内,安然无事,你着急也没有用。有一回,我有紧急任务赶往惠安崇武,需要搭上去泉州或去青阳的班车,之后,转车惠安或崇武,但无论是从石狮还是安海方向开往泉州或青阳的班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却是没有一部停下来的,我急了,只得请求车站人员帮忙,开始他并不理睬,后来见我确实是“军情紧急”,答应帮忙,自己横到路中央,才将一部从安海来的过路车拦了下来,救了急,而我在匆匆上车时候,却是忘了感谢,现在想来,犹有愧意。
晋江当时处在福建前线的重要位置,公路算是高等级的。而所谓高等级公路,就是一条大约三至四个不分左右车道的沙石路面的公路,路边两排密密的木麻黄,也是战备的需要,便于隐蔽部队行动的车辆。从福埔到青阳不到五公里的路段上,木麻黄高大浓密,像是两道穿不透的绿墙。两地的距离虽近,往往却是搭不上车,纵然是青阳,晋江县的县城,一天也发不了几班车,大多是泉州发往石狮、金井或安海的过路车。青阳车站比福埔车站要大一些,但也是路边站,在一个坡地上,汽车进站出站均要上坡与下坡,停车场就像一间大通道,架子顶上盖着灰瓦,但遇风雨尤其是台风季节,停车场照样风雨飘摇,没有多少的安全感,更别想有个候车室,有张靠背椅坐坐。
从福埔至青阳,在搭不上公共汽车的情况下,还有一招可供选用,就是招呼路边的单车(自行车),这种经过改造的单车,卸去标配的后架,换上铁匠铺加工的宽大而结实的铁架,并且斜插了一柄木棍,如载人,可扶手,如载货,则固物,车手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可人货混用,要么载人要么载物,一般情况下,载人多于载物。好几次上青阳,怎么也拦不下公共汽车,只得坐单车,屁股下倒是不硌,细心的车手会在铁后架铺上一块麻袋片或是半个蒲包,坐上去还是舒适的,但若有汽车从你的身边呼啸而过,则就要吃一些苦头,那飞速而过的汽车卷起的一溜沙尘,立时便会让你睁不眼睛,呛得你透不过气来。就是这样,那单车的速度却是不减半点,想想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打拼精神吧。
露天电影场
七十年代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青阳镇上只有一家人民会场,可供放电影或演出,所看的电影也只有“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与《平原游击战》)之类,高甲戏多为传统剧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也都封了。当年经常放映的香港片,只能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位于罗裳山的师部,文化生活相对要丰富一些,电影每周必放,所放之片,与青阳电影院还有所区别,因为罗山师部电影片的配给,属于军队系统,一些进口片,比如朝鲜片《鲜花盛开村庄》、阿尔巴尼亚《桥》等都比青阳要早很多,那时,看朝鲜片与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今日看美国大片还要热闹。革命样板戏是文革时期精心培育的,但青山、包括罗山师部也是看不到的,只能看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但那比真正的样板戏相差太远。后来,为了普及样板戏,便搬上银幕,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原班人马,原汗原味。这些片也都首先在部队上映,并且是以跑片的速度上映,接连不停地放。记得我第一次看《白毛女》,便是从傍晚一直看到第二天的清晨,一连看了三场,先在罗山师部,之后,跟随电影组的放映车,在灵秀山的团部看第二场,再到宝盖山团部看第三场,当第三场《白毛女》“天亮了”之时,露天放映场也天亮了,一夜的文化饱餐,用现在的话说是“看通宵电影”,全无睡意,兴奋得不得了。
罗山师部也有一个大礼堂,但只要不下雨,每周一次的电影,都安排在露天电影场放映。所谓露天电影场,是以条石依山而建,台阶式,呈半圆形,迎面是一堵白墙,临时架起的座机,将图像投在白墙上。露天电影场放映,师部的军训科会按老规矩留出一些座位给驻地群众,师部则按建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师医院、师直等依次列队而坐,等候电影开场时,各个建制单位起劲的拉歌,什么《说打就打》《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看谁唱得好,声音大,只要听到歌声,附近村庄的年轻人便知道今夜“有戏”,匆匆吃过晚饭后,便也陆续坐到留给他们的位置上,如果是新片,比如《卖花姑娘》之类,青阳的年轻人也会骑了单车赶来。
我不知道在这个露天电影场看过多少场电影,师政治部的位置是在放映机的左边,与师医院靠在一起。那时,师部只有师医院有女兵,所以,师医院的列队一出现,全场注目,我那时正与师医院的小周护士悄悄地谈恋爱,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有一次在露天电影场上,记不得看什么电影了,天气冷,大多数人都穿了棉大衣,而师医院的女兵们为了漂亮穿得却单薄,就在大家叫冷的时候,忽然师医院有个“稍知内情”的人提议:“王干事(我当时的职务),把你的大衣借给周护士穿穿。”虽然我很乐意这样做,但当时却是严肃地拒绝了,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政治部的王干事将大衣借给医院的周护士,那不就等于公开了我们的悄悄恋情?那年代公布不成熟的恋情是极其危险的,不腰折才怪呢。我当时果断而无情的决定,保住了我们的爱情。虽然后来成为妻子的周护士常常以此取笑王干事小气,也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1996年夏天,我携全家重返罗山师部,那时露天电影场尚在,一家三口站在青苔斑斑如罗马斗兽场般的石阶上,感慨万千。如今这个露天电影场在修建世纪大道时切去了大半,不知道还能不能寻得一两级青褐色的台阶?
一个人的海滩
晋江有漫长的海岸线,三面被二湾(泉州湾与深沪湾)与一澳(围头澳)环绕,七八十年代,石狮包括永宁与祥芝都属晋江县,有着丰饶的海岸资源。不过,那个时候不但不能开发,甚至连到海湾的沙滩走走也会受到限制。比如围头最前面的突出部叫乌岗头,与金门就特别地近,我曾有几次站在那群巨大的礁石上,用普通望远镜观察,对岸的地形地貌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对方守军到阵地上巡逻,也都数得清人头,观察所的哨兵,还给他们编上号,根据规律,都可以排出他们的巡逻时间表。
正因为离国民党的驻军离得近,所以,晋江的海岸线基本都驻扎着部队,海滩成了军事区或准军事区,许多地方都立有这样的牌子:“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实际上除军人之外,其他均被视为闲人了。
其实,我当时可算是一个“闲人”,在基层连队写报道,指导员把我当作上级机关的人,可以不出操、不站岗、不参加军事训练、甚至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有兴趣则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巡游海岸沙滩,因为我是军人,就是在沙滩玩着闭逛,也不被视作闲人。有好几次,晚餐之后,落日余辉之中,我一个人在一大片的沙滩上行走,偌大的一个海滩,竟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其如永宁的将军山海滩,我记得非常的平坦辽阔,金黄的沙滩上,一大排挡风沙的木麻黄,我总是一个人出没沙滩,累了便躺在木麻黄的树下,旁边是成片的开着黄花的海芙蓉。有一次,我一个人钻进碉堡中偷偷的看从连部封存的图书室找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看就是一天,竟是忘了吃饭,连队也没有人注意到。现在这里也已经成了旅游区了,碉堡也成了旅游景点,有一次我陪同内地前来旅游的朋友说,当年这片沙滩只属我一人,他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说那太奢侈了。而对于我,面对人头蹿动的游客,却是全然找不到当年一个人独享沙滩的感觉。
有一个发生在我们同行中间的故事:一天,《解放军报》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篇通讯,描写某守备部队在风雨之夜抓到了一个从金门方向爬上岸来的特务。通讯刊出后,反响很大,引起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注意,但一查,有关部门却是没有接到此类的报告。于是便追查下去,质问福州军区抓了特务为何不报告总部?福州军区也纳闷,于是追查这个守备师,师里也觉得奇怪,一个电话打到团里,团里说他们也没有听说,最后把那位写通讯报道的作者找来,作者理直气壮,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正下暴雨,有一个人却坐在海边的礁石上,那里可是军事禁区,哨兵便将他抓了。原来,他将一个进入“军事禁区”(也就是坐在海湾的礁石上吧)的人,说成了从海里爬上来的特务,可见那时的“敌情”观念。
邓丽君与三用机
晋江由于是著名的侨乡,众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侨,经常回国省亲,他们带来了外汇与洋货,只要海关稍微放松一点,洋货便乘隙而入。70年代末,有政策规定华侨回国,可以带回一至二件大件的电器,如电视、冰箱、三用机、摩托车之类,这一政策性的松动,使得晋江一夜之间突变,不少的店铺摆上了小件的进口电器,不少的家庭都持有了彩色电视、三用机,待价而沽。尤其是随着三用机的进入,录音磁带也纷纷登陆,而在众多的音带中,邓丽君歌带最受欢迎。华侨家属在出售三用机时,一般需要配带10盘磁带,而邓丽君歌带的比例,往往在销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一段时间,青阳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邓丽君甜甜的歌声(那时尚被指责为“靡靡之音”),甚至在西滨、陈埭、金井等乡镇的华侨屋子里,也是邓丽君的歌满天飞:《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等等等等。
我那时已经离开了晋江,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工作,但我的妻子还在罗山师部医院。两地分居会有很多的麻烦,但也为我回晋江寻找邓丽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曾经一次次地从罗裳山骑了单车到青阳镇,不是在店铺而到华侨的家里,寻访北京、上海等地文艺界的朋友所需要购买的三用机(集录音、收音与播音于一体的机器),三洋四喇叭4500是最受欢迎的品牌,每一台机最少要搭配邓丽君的音带2盘,还有索尼的六喇叭,价格就要贵多了,搭配的音带更多,尤其是邓丽君的音带必须在5盘以上。我不知道为外地的朋友,代购过多少台三用机,包括总政歌舞团、海军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总政文化部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也都是最先从晋江获得邓丽君的信息与歌声。当时福州军区文化部长曹欣(电影《上甘岭》的作者之一)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他的夫人时常把我找去,关着门听邓丽君的歌,也和北京来的朋友一起听过。当时,听着邓丽君甜蜜且带沙哑的歌声,灵魂都为之振动,别说对于唱惯了听惯了“说打就打”这种硬性与血性歌的军人,就是不少专业人员,也没有想到,词可以这样写,歌可以这样唱,声可以这样发。现在看来,这真是一种启蒙,是一种轻音乐、流行歌曲的启蒙,甚至是一种思想的启蒙,而这种启蒙的源头却是在晋江。
邓丽君对我而言,不仅是启蒙还是一种怀想。那些年,邓丽君的歌带,我几乎是收全了,直到现在还保存了几盘经典的盒带。而我最喜爱的是邓丽君唱的《夜来香》,我曾对军人妻子说过,如果我当指导员,我将带领全连的士兵齐声高唱这首歌,你看多好听多有韵味:“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在新婚的日子里,我们已经有了一台两喇叭的索尼三用机,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音带数盒,有《海韵》深情而浪漫的相伴。当然,晋江让我所接触到的还不仅仅是邓丽君与三用机,我不仅在青阳,还会到陈埭、西滨、安海等地走村串户,墨镜、折叠伞、电子手表、带有防水功能的“西铁城”手表、计算机、丝袜等等,都是从这里得到的。我的妻子曾舍得花30元钱,在青阳的一家店铺买下了松下牌的电动剃须刀,也曾为岳父大人在西滨一个华侨家买了一台日立牌14英寸的彩电,价格为1500元,相当于我三年工资的总和。
那时的晋江,什么都是好的呀,遍地都是“宝”啊。只要一走入青阳的小巷,便会变得神秘而激动。多少年后,我曾下榻青阳一家豪华的酒店里,入夜时分,一人悄悄地隐入夜色之中,可在夜色的灯光里,我完全不认得当年的大街与小巷,好不容易拐到一条小巷,依稀可见当年的景象,红砖墙,石门框,只是物换人非,已经没有了当年寻找三用机与邓丽君的感觉了。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