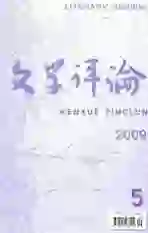明代前后期之南北曲盛衰观
2009-01-08赵义山
赵义山
内容提要论述明散曲发展史,人们一向以昆曲兴起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普遍认为:在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昆曲流行之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或谓北曲“巳成余响”。笔者经过考察后发现,在昆曲未盛以前,南曲已非常兴盛,倒是北曲不敌南曲,已出现衰势;在昆曲兴盛之后,无论在歌坛的演唱和作家的创作中,北曲不仅都没有消亡或成为余响,而且还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散曲学是一个相对冷僻的学科,在散曲学中,元散曲的研究差强人意,而明清散曲的研究过去一直较为岑寂,不仅一些重要的曲家被长期冷落,即便是一些有关散曲发展演变的重大事实,也还未能得到正确认识和客观论述。例如,对明代前后期(即昆曲盛行前后)的南北曲盛衰演变,曲学界的认识便与明散曲发展演变的基本事实不符,澄清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对明散曲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明清散曲发展史的认识,以及对明代如戏曲、俗曲和词等相关文体发展演变的研究,也都有重要意义。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南北曲,主要指散曲,尽管所引材料和对有些问题的分析有时不免包含了戏曲腔调,但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散曲;又,对于“昆曲”与“昆腔”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昆曲的形成与演化等问题,学界早有论说,故不拟涉及。本文将立足文献记载与作家现存作品,从歌坛演唱与曲坛创作两个方面考察昆曲兴盛前后的南北曲盛衰状况,以获得一个正确认识。
一明代前期的南曲盛衰观
明代前期南北曲的演化发展,按任中敏先生《散曲概论》的说法,是“明代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任先生虽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即未有昆曲以前,北曲盛于南曲。从任先生的具体论述看,他所说的“未有昆曲以前”,具体指的是嘉靖(含嘉靖)以前。自从任先生作出这个论断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的散曲史论著,凡论及明前期南北曲盛衰者,大都祖述此说,一些较有影响的散曲史著作甚至说得更为明白:“在昆腔未兴盛前,北曲是曲坛主流,而南曲亦渐兴”。对昆曲未兴盛以前,南曲不如北曲之盛的看法,曲学界一直未见异议。在昆曲未兴盛以前(嘉靖以前),南曲果真不如北曲兴盛吗?要澄清这个事实,无非通过两条途径:第一是检索明人的记载,第二是考察明代曲家留下的作品l笔者已通过这两个途径,考察了成化、弘治间南曲兴盛的事实,现在再着眼于整个“未有昆曲以前”(由明初到嘉靖以前)的明代前期,仍由明人记载与现存作品来考察南曲在歌坛演唱和文人笔下的盛衰事实。
先看明人记载。翻检明代曲论家有关南北曲的论述,笔者迄今尚未发现“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一类的明确记载,只是有些曲论家们的表述,容易引起误解,给人造成一种在嘉靖以前南曲不如北曲兴盛的印象。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记载和论述,主要有两种著作,一是徐渭的《南词叙录》,二是王骥德的《曲律》。《南词叙录》是第一部论述南曲的专著,在曲论史上极受重视,其论及明中叶以前南曲之发展状况,主要有以下4条材料:
国朝虽尚南,而学者方陋,是以南不逮北。然南戏要是国初得体。南曲固是耒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则《玩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种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夸人时文气。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
《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
本朝北曲,推周宪王、谷子敬、刘东生,近有王检讨、康状元,余如史痴翁、陈大声辈,皆可观,惟南曲绝少名家。《南词叙录》书前有作者小序,署“嘉靖已未夏六月望”,可知该书成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从徐渭所说“元末、国初”算起,到他写《南词叙录》时,已历200年,由徐论可知,南曲在这200年间的发展,有两大矛盾冲突:一是“时尚”之好与文人传统观念的冲突,二是“本色”(俚俗语)与“文雅”(时文气)的冲突。时尚与传统的冲突,无疑表现出市民新的审美趣尚与文人崇古积习的矛盾;。本色”与“文雅”的冲突,表面上是文人创作趣尚的不同选择,是媚俗从众还是表现作家自我的才情,但实质上仍表现的是时尚之好与文人自我意识的矛盾。二者矛盾冲突的结果怎样呢?按徐氏的说法,是“南不逮北”。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的是“时尚”的引力反不敌文人的好恶?还是徐渭别有偏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南不逮北”做如何理解:徐氏的意思究竟是说“南曲不如北曲(盛行)“呢?还是说“南曲不如北曲(雅致)”呢?抑或是说“南曲不如北曲(地位高)”呢?他没有说明白,似乎可以多解。如果照第一种理解,则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判断;如果照后两种理解,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才能作为我们认识南北曲孰盛孰衰的依据,是价值判断,便只能作为我们认识徐渭及同时代人曲学观念的依据了。那么,徐渭的话究竟是一种事实判断呢?还是一种价值判断?假如孤立地看这一处,实难断定,如果结合徐氏别处对南北曲的比较论述,便不难理解。徐氏一则曰:“至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二则曰:“胡部自来高于汉音”;三则曰:“今日北曲,宜其高于南曲”;其崇北卑南的态度,何其鲜明!正是因为崇北卑南,使他用高看北曲的眼光俯视南曲,遂觉得南曲有许多的卑陋之处,甚至在论说中不顾自己持论的前后矛唇他一方面赞扬《荆钗》、《拜月》数种的“稍有可观”,而对“其余皆俚俗语”的南曲作品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赞赏“其余皆俚俗语”者“句句是本色语”,而对《香囊记》“以时文为南曲”的雅化倾向大加批评。由此可知,徐渭对于南曲发展状况的论述,诸如“南不逮北”、“惟南曲绝少名家”等等,其实都表明的是他对南曲的一种卑视态度,是代表着当时舆论的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而并非客观的事实记载。既然如此,我们就无法从《南词叙录》的记载中得出嘉靖前南曲不如北曲盛行的结论,此其一。
其二,倒是从《南词叙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嘉靖前南曲已经很兴盛的事实。首先,徐渭明确记载:“国朝尚南”,按“美生于所尚”(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自序》)的一般原则,既然明初人已崇尚南曲,南曲焉有不盛之理?其次,据上文所引,徐渭在批评《香囊记》“以时文为南曲”,“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后,紧接着又批评“效颦”《香囊》者变本加厉,更加讲究文采与故事,无毫发宋元南戏的韵味(“无复毛发宋、元之旧”),再接下来,徐渭便批评“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以至于使这种“以时文为南曲”的风气“遂至盛行”。由这些记载可知:在嘉靖以前,“以时文为南曲”的风气已经非常“盛行”,这种风气“盛行”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南曲戏文的盛行;而
南曲戏文的盛行,无疑又是以南曲的盛行为前提条件的。
再说王骥德的《曲律》。此书是古代曲论中最具系统性,而且理论水平最高的一部散曲剧曲兼论的著作。在《曲律》卷三十九《杂论》中。王氏有一段关于南北曲作家创作的著名论述:
近之为词者,北词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蜀则杨状元升庵,金陵则陈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东则李尚宝伯华、冯别驾海浮,山西则常廷评楼居,维扬则王山人西楼,济南则王邑佐舜耕,吴中则杨仪部南峰。康富而芜;王艳而整;扬俊而葩;陈、胡爽而放;徐畅雨未汰;李豪而率,冯才气勃勃,时见纰颣,常多侠而寡驯;西楼工短调,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谐谑,杨较粗莽。诸君子间作南调,则皆非当家也。南则金陵陈大声、金在衡,武林沈青门,吴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龙,而陈、粱最著。唐、金、沈小令。并斐亹有致;祝小令亦佳,长则草草,陈、梁多大套,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伯仲间耳。馀未悉见,不敢定其甲乙也。
王骥德共论述了18位明中叶散曲作家,被其认定为“北词”(北曲)作家的有12位,南曲作家只有6位,乍一看来,给人的印象显然是南曲不如北曲之盛,但其实并非如此。在王骥德所论述的12位北曲作家中,其存曲较多,历来为论者瞩目而作为主流作家论述的,有康海、王九思、杨慎、李开先、冯惟敏、常伦、王磐等7人,在这7人中,除王磐一人专作北曲外,其余6人都是南北兼擅的曲家,而且有大量南曲作品存世,并非只是“间作南曲”,如康海现存南曲作品49首,王九思215首、杨慎203首、常伦45首,李开先216首、冯惟敏201首。而且,其中有的作家北曲极少,如李开先的北曲才16首,杨慎38首,就南北曲的比例说,这两位基本上可以说是南曲家。倒是王氏所记载的南曲作家中,如唐寅、沈仕、祝允明,梁辰鱼等人,才基本上是专作南曲的作家,只有陈铎、金銮两人南北兼作。总起来看,在王骥德所论述的能进入主流作家行列的13位明中叶散曲作家中,其专作南曲的有4人,专作北曲的仅1人,而南北兼作的有8人,如果从南北曲作家构成看,倒是南盛于北了。如果从现存作品构成看,这13人共有南北曲作品约3100首(套),其中北曲作品约1730首(套),南曲作品约1370首,两者相差300多首,但其中被王骥德认定为南曲作家的陈铎,北曲作品却多达456首(套),南曲反而才114首(含南北合套),如果除开这个特例,南北曲是基本持平。因此,从王骥德的记载中,我们也无法得出嘉靖以前北曲盛于南曲的结论。
倒是从王骥德《曲律·论曲源》一节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明万历以前南曲盛于北曲的论述:
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始犹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成弃其捍拔,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
王骥德《曲律》完成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所说的“迩年以来”,究竟是万历以来?还是嘉靖以来?还是更早?王氏未能言明,暂且不论。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以王氏的眼光看来,入明以来,南北二曲一直是“画地相角”,各擅胜场的,到“迩年以来”,则是南盛于北,从来没有“北盛于南”的。王骥德所说“迩年以来”究竟指的哪个时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先看看他在前面论述明中叶散曲18家时提及的“近之为词者”这一时间概念,因为这个“近之为词者”,与他说的“迩年以来”,两者出一人之口,可供参考。在“近之为词者”中时代最早的上限作家陈铎,活动在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期的曲坛,时代最晚的下限作家梁辰鱼,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去世,两者之间约有120年光景,可见王骥德所说近年以来,原本可以指成化、弘治以来,直到万历初年的一个大致时间段。也就是说,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和万历初年,都有可能是王骥德所说的南曲盛而北曲衰的时代。那么,有没有比王骥德说得更确切一些的呢?有的,这就是刘良臣(1482--1551)的《西郊野唱引》:
正德以来,南词盛行,遍及边塞,北曲几泯,识者谓世变之一机,而渐移之。移之,诚是也;世顾以为胡乐而鄙之,岂其然哉!
刘良臣,字尧卿,号凤川,山西芮城人,弘治辛酉(1501)举人,数上公车不第,授扬州通判。后改官平凉。又数年,因以直道忤当路,遂告归家居,卒于嘉靖二十九年(1551)。其著有散曲集《西郊野唱北乐府》存世。考其曲作活动,恰好在正德、嘉靖间。观良臣所记,与王骥德“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成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的说法,简直如合符契!只不过刘良臣说的时间要比王骥德更为确切而已。良臣以正德、嘉靖时人,道正德、嘉靖时事,而且以曲家身份,道曲坛之事,言之凿凿,应为学人采信。如果把刘良臣的记载,与前引徐渭,王骥德等人的论述结合起来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明初以来,在歌坛的演唱中,人们逐渐好尚南曲,于是南北二曲并驾齐驱,由正德(1506—1521)到嘉靖(1522—1566)时期,南曲盛行全国,北曲走向衰落。
以上是就明人有关南北曲盛衰的记载而言,现在再看嘉靖以前曲作家们的创作。前文在分析王骥德《曲律》的记载时,已考察了明中叶13位主流曲家。现在,我们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所谓“未有昆曲”的嘉靖以前(含嘉靖)的所有曲家。如果依据谢伯阳先生《全明散曲》的收录,在粱辰鱼之前,有散曲存世的作家共141人(不含梁辰鱼),如果把由元入明的王子一、兰楚芳、汤式等人除去,可以真正算做明代前期的散曲家共有128人,其中,专作北曲者41人,专作南曲者51人,南北兼作者36人,从作家构成情况看,显然是南盛于北。从作品构成看,前期128位作家共存曲约4660余首(含套数,后同),其中北曲作品约2790首,南曲作品约1870多首(含南北合套32篇),北曲作品多出南曲作品900多首,似乎是北盛于南,但是,其中只不过有3位南北兼作的曲家,其北曲明显偏多:一是朱有燉,存北曲290首,南曲只有29首;二是被王骥德等推为南曲代表作家的陈铎,存北曲456首,南曲只有114首,三是康海,存北曲249首,南曲只有49首;这三位南北曲兼作的曲家,共存北曲995首,共存南曲189首,他们三人的北曲比南曲多出800多首,与整个前期北曲作品多出南曲作品的900余首大体相当。前期共128位作家,恐不能仅凭这三位曲家的北曲数量陡然多于南曲,就得出“北曲为盛”的结论,何况还有作家构成的南盛于北呢!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是,北曲在当时已逐渐由歌场走向案头,一些文人在“北曲高于南曲”的潜意识支配下,多选择北曲抒情写意,并将其收编于自己的文集,因而容易得到保存,但大量词场应歌的南曲作品,文人多随手付与歌儿,则很容易散失;因此,盛行歌场的南曲,肯定不如走向案头的北曲易于保存,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另外,如果要从南北曲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着眼的话,那无
疑属于现代人价值评判的话语,离前人着眼于曲运盛衰意义上的南盛于北,或北盛于南的含义,已相去很远了,故此处不拟讨论。
总之,结合明人的记载和曲坛实际情况考察,关于明代未有昆曲以前南北曲盛衰的事实应当是:从明初到弘治以前,是北曲渐衰而南曲渐盛的时期;随着时尚之好,从正德到嘉靖,是南曲盛过北曲的时期。也就是说,南曲在“未有昆曲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就已经盛于北曲了。嘉靖以后,随着昆曲的盛行,南曲成压倒优势,北曲则进一步走向衰落。既然无论从明代人的记载中,还是从曲家的实际创作中,都难以得出“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的结论,但为什么人们一向又有这样的认识呢?揆其原因,窃以为有两点:其一,由于明人分南北曲论作家创作,有很大局限,容易使人在理解上产生偏差;其二,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人们无以对文人的散曲创作做全面的分析与考察;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人们一直误以为“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
二明代后期的北曲盛衰观
对于明中后期南北曲的盛衰变化,任中敏先生认为:“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矣!”此论一出立即获得同时代人一致认同,如卢前先生亦谓:“昆腔以后有南词,而北曲亡;北曲亡即曲之亡矣。”郑振铎先生也说:“从嘉靖到崇祯是南曲的时代……北曲的作家几至绝无仅有。”粱乙真先生也说:“到了昆腔起来以后,其情形便大不相同,这时南曲大盛,而北曲便渐就衰灭,久不复现于散曲坛了。”大约半个世纪后,一些朋友仍承此说,如谓“昆腔兴起以后,南曲乃成曲坛主流,北曲则已成余响”。南曲成曲坛主流,早在昆腔兴起以前,不必等到“昆腔兴起以后”,前已有说。这里要检讨的是“昆腔兴起以后”,北曲是否真的“已亡”或“已成余响”?
要检讨“昆腔兴起以后”(即嘉靖以后),北曲是否“已亡”
或“已成余响”,无非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歌坛的演唱,另一方面是作家的创作。假如北曲在晚明确实已经基本退出歌坛了,而且基本没有人再创作北曲,或者仅仅是极少数人偶一为之,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北曲已成余响”,如果说得严重些,可以说北曲“已亡”。但是,假如北曲还在歌坛继续传唱,也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而且,曲作家们还在大量地创作北曲并表现出相当的实力,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恐怕就不能说北曲“已成余响”,或者说北曲“已亡”了。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看歌场的演唱。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中曾记载说:
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童习唱,一时优入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蒜酪遗风。予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弦索,今绝响矣。何又教女鬟数人,俱善北曲,为南教坊顿仁所赏。顿曾随武宗入京,尽传北方遗响,独步东南,暮年流落,无复知其技者。
这是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北曲还在歌坛传唱的明确记载,沈氏所言“今绝响矣”,又是在什么时候呢?考沈德符生于万历六年(1578),其所作《野获编》,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自序,可见所谓“今绝响矣”的“今”,当在万历后期。既然沈德符这样记载了,所以又不免让人觉得北曲从此退出歌坛了,“绝响”了。这样理解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看看沈德符别的记载,自然就会明白。同样是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沈德符又记载说:
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调几废,今惟金陵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而吴中以北曲擅场者,仅见张野堂一人,故寿州产也,亦与垒陵小有异同处。顷甲辰年,马四娘以生不识金阊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巧孙者,故马氏粗婢,貌奇丑而声遏云,于北词关捩窍妙处,备得真传,为一时独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还曲中即病亡,诸姬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
今南教坊有傅寿者,字灵修,工北曲,其亲生父家传,誓不教一人。寿亦豪爽,谈笑倾坐。若寿复嫁以去,北曲真同广陵散矣!”
由沈氏所记可知这样几点:第一,北曲的演唱在万历后期还有“北派”一说,相对而言,就应该还有演唱北曲的“南派”,而“北派”的jE曲演唱还有金陵、汴梁、云中等地域流派,由此可见,在万历后期,北曲的演唱还很盛行并有相当的势力。第二,一个马四娘尚且可以带“其家女郎十五六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可见万历年间的吴中地区虽然已经是南曲的天下,但北曲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否则,那“北Ⅸ西厢》全本”唱给谁昕呢?第三,北曲还有如马四娘、巧孙、傅寿这样一批身怀绝艺的明星演员,而且像傅寿这样的明星演员还很年轻,尚未“嫁去”。由此可知,在万历后期,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书的1610年前后,北曲是实实在在地流行着、传唱着,不仅没有退出歌坛,而且还有相当的实力和群众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前文沈德符所言“绝响”的问题。既然沈德符记载了北曲在万历后期还很盛行的事实,怎么又说“今绝响矣”呢?这不明显矛盾吗?其实,只要细审前文,便不难发现,沈氏所言“今绝响矣”,并非针对整个北曲的演唱,而是说何元朗(名良俊)亲自调教的身怀歌唱绝艺的几位“家童”,其高超的演唱技艺,无人承传,而今已成“绝响”了。打个比方说,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高超的京昆演唱技艺,由他的高足蔡正仁继承下来,假如蔡先生未能把俞先生某门绝活传下去,熟悉俞、蔡二位表演的老票友们就会感慨:俞派的某门技艺已成绝响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整个昆曲演唱就已成“绝响”了。这道理很简单,不用多说。
在沈德符的记载中,还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如马四娘来吴中的时间:“甲辰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尽管她不久去世,她所带的弟子,结果是“诸姬星散”,她苦心培养的最善唱的巧孙也“去为市妪,不理歌谱”,但这些人的北曲演唱技艺绝不会立即失传,一有机会,她们会复操旧技。还有那个正在南教坊唱北曲的傅寿,暂时还没有“嫁去”呢,这些人再怀技二三十年,应该不成问题,由此推考,到崇祯(1628--1644)末年明亡,北曲完全有可能在曲坛继续演唱。如果要说“北曲已成余响”,根据以上的考察可知,这最早也要等到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年间,而绝不会在“昆曲起来以后”的隆庆(1567--1572)或万历(1573--1620)年间就成“余响”的。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北曲在明末天启,崇祯间的歌坛成为“余响”,最多还只表现在吴中地区,至于广大的中原地区,那还另当别论。还有,即使在吴中地区,这种成为“余响”的事实,也最多只表现在市井流俗这个层面,至于一些文人雅士的曲唱活动,则依然保留着对北曲的浓厚兴趣。比如,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的散曲家施绍莘(华亭人),因闲居于乡,日以饮酒赏花、赋诗作曲为乐,他的散曲集《秋水庵花影集》
中便记载着他曾作有不少北曲付歌童演唱的事实。如北【正宫·端正好】《春游述怀》套《跋》文有云:
余雅好声乐,每闻琵琶筝阮声,便为魂销神舞,故迩来多作北官,时教慧童,度以弦索。更以箫管叶予诸南词。院本诸曲,一切休却。
又,其北【双调·新水令】《夜雨》套后所附陈继儒《跋》有云
子野曾于秋梧雨馆,令小童以单筝度之。文既凄然,声复哀怨,遂觉窗外潇潇,点点是泪。
又,其北【南吕·一枝花】《送春》套后自《跋》有云:
“送眷”两字,无限伤心。已谱南官,付之箫管;复缀是词,并被弦索。凄凉悲壮,始各极其致。每歌此词,大都在落红飞絮中。
据笔者考察,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中之曲,多作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到天启六年(1626)之间,在这期间,他调教的家养歌童尚能以弦索度北曲供其欣赏,那么,这些歌童再给他唱10多年北曲,直到崇祯末年,该不是什么难事吧。而就施绍莘的个人爱好而言,又最喜欢听北曲:“每闻琵琶筝阮声,便为魂销神舞,故迩来多作北宫”。由此可知,在施绍莘等文人雅士的歌舞筵前,北曲不仅没有成为“余响”,而且在不少时候还与南曲分庭抗礼,同样成为—种“主音”。
综上所述可知,在万历以后,从歌坛演唱的情况来看,北曲不但并没有消亡,而且还相当盛行,因此,如单就歌坛演唱而言,说“昆曲之后,只有南曲,北曲亡矣”,或云“北曲已成余响”,此论是大可商榷的。
考察了歌坛的情况,接着再看曲家的创作。在昆曲盛行以后的晚明曲坛,即由隆庆经万历、天启而至崇祯的60多年里,除了梁辰鱼、沈璟、王骥德、张凤翼、陈所闻、施绍莘、胡文焕、周履靖等南派曲家以外,还有薛论道、薛岗、王寅、王克笃、赵南星、丁彩、丁惟恕等北派曲家,他们还创作有大量的北曲。试看:
薛论道(1531?—1600?),字谭德,号莲溪,别署莲溪居士,直隶定兴(今河北易县)人。幼时多病,一足残废,喜谈兵,京师公卿呼为“刖先生”。从军30年,屡建奇功,因遭疑忌,未能腾达,颇为失意。《康熙保定府志》、《乾隆定县志》等有小传。著有散曲集《林石逸兴》,存小令1000首,是散曲史上存曲最多的曲家,内中有北曲小令346首。
薛岗(1535?—1595),号歧峰,别号金山野人,山东益都人。或将其与同郡冯惟敏并称,谓“冯君骚雅,薛君壮丽”。所著有《金山雅调南北小令》一卷,存小令105首,内有北小令44首。
王寅(?一1585以后),小名淮孺,字仲房,一字亮卿,号十岳,安徽歙县人。所著有《王十岳乐府》,存曲125首(套),内中北曲113首(套),曾自序其集,有云“予此册之梓,用传中原名家”。
王克笃(1526?—1594后),字菊逸,山东寿里(今东平)人。著有散曲集《适暮稿》1卷,今存曲143首(套),内有北曲112首(套)。其咏物诸曲,多有可观。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署清都散客,直隶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明史》有传。南星是晚明模仿时尚小曲最成功的曲家之一。所著有《芳茹园乐府》,今存曲60首(套),内中北曲与时尚小曲有35首(套)。
丁彩(1573?—1637后),号前溪,山东诸城人。雅好词曲,著有《小令》一卷,今存114首(套)。丁彩和赵南星一样,也是晚明模仿时尚小曲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其集中之曲有相当部分为时尚小曲和北曲。
丁惟恕(?—1640后),字心田,山东琅邪(今诸城)人。所著散曲有《续小令集》,收南北小令凡205首,内中有北曲86首。其集中有30多首题为【河南韵】的小令,当是模仿河南民间小曲之作,其言情、咏物、写人、记事,多嘲弄戏谑之笔,甚有曲趣。
上述北派诸家,与梁、沈南派曲家相比,其曲风普遍质朴豪放,尤其是薛论道之曲,豪气干云,更有一种金戈铁马般的气势,如:
腥膻何敢易天朝,颇牧山林装睡着。九重但肯颁一诏,把燕台增尺高,论割鸡焉用牛刀!轻踏碎单于道,慢折磨可汗巢,贺兰山瓦解冰消!
(北【双调·水仙子】《宿将》四首之四)
拥旌麾鳞鳞队队,度胡天昏昏昧昧,战场一吊多少征人泪!英魂归来归?黄泉谁是谁?森森白骨塞月常常会,冢象碛堆朔风日日吹。云迷,惊沙带雪飞,风催,人随战角悲。(南【商调·山坡羊】《吊战场》)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边波千丈I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
(北【双调·水仙子】《愤世》四首之一)
前首北曲抒写将士的报国雄心,中间一首南曲描写战骨抛荒的悲凉情景,这类边塞之曲是以前的散曲创作中很难见到的内容,显示了薛论道对散曲题材内容的开拓,后曲感叹仕途中争名夺利的残酷和危险,以及小人得势,奸臣当道,胡作非为,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薛论遭之曲的豪放质朴、曲味浓郁,不仅可与康海、冯惟敏等明代一流的豪放作家抗衡,即使置于元人马致远、贯云石等豪放一派中,亦无愧色!另如薛岗、王寅等人,也有大量富于曲味的佳作,如:
滔滔海洋,流通地脉,派出天潢。苍波万倾无遮障,纳汉吞江。接日窟鳌头殿广,泛星槎鲸口帆张。蓬莱上,神仙密访,放荡水云乡。(薛岗北【中吕·满庭芳】《望海》二首之一)看学术纷纷,知谁假谁真?假多真少笑时人,总歪传画本。是真是假难评论,价高价减随人信,大家跳入面糊盆。请先生自忖。(王寅北【正官·醉太平】《十二首自咏》之七)
只说你踢飞脚蓦过了华山颠,只说你打跟斗跳过了黄河堰,只说你吼一声神鬼惊,只说你睁眼魔王颤。原来你逞豪强没天日,全不管结怨仇有万千。饶你有楚霸王拨山力,也须索到乌江少渡船。三年,把一首拳喻篇成先见,今年,把几个猛士们着了拳。(丁彩北【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眼看着六十生辰,琴也宜人,棋也宜人。回想想五十光阴,诗也曾亲,酒也曾亲。静观他荆篱外风尘乱滚,一任他市朝中人海浮沉。匿迹山林,深闭柴门,隔断红尘,占住白云。(丁惟恕北【双调·折闺令】)
这类曲子,无论其写景、叹世、言隐,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壮景豪情、逸怀豪兴和本色俗趣,使北曲的“蒜酪”遗风、大俗之美,继续得到发扬。总之,隆庆、万历以后,以薛论道、薛岗等人为代表的北派曲家,其涉题宽广,他们不仅作有大量北曲,而且无论其南曲北曲,都呈显出北派曲家特有的豪迈粗犷一格,曲风质朴豪放,曲趣最富,继承盛元之音最多,实为明后期散曲文学中最正宗一格,仿佛明后期曲坛灿烂的晚霞!
综上所述可知,在昆曲兴盛以后的明后期,北派曲家的北曲创作,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质量方面看,都还有很了不起的成绩!事实昭然俱在,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言之凿凿,谓“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呢?或谓“昆腔兴起以后”,“北曲则已成余响”呢?我想,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明代中后期,薛论道等北派曲家却与晚明江南曲学之士毫无交往,其曲又多为抒怀写意之作,未尝被管弦流播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故晚明诸论家未置一词,由此而多被后世论家忽略。第二,前辈学人如任中敏先生、卢前先生等,他们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未能见到嘉靖、万历以后一些北派曲家的作品,如薛论道的散曲集《林石逸兴》,这部刻于明万历间的曲集,存曲千首,不仅是中国散曲史上存曲最多的散曲别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边塞军旅题材在散曲史上独树一帜,其豪气干云之调、金戈铁马之声,可谓古今独步!但任中敏先生当年编辑的《散曲丛刊》和卢前先生编辑的《饮虹移所刻曲》(正编)都没有收入这部重要曲集。任先生虽然在《散曲概论·书录》中提到了《林石逸兴十卷》,但注云:“见《莼歔诗话》”,可见任先生当年确实未曾见到这部重要的散曲别集。连薛论道这样重要的曲家都被忽略,那么,北派其余作家,自然就更难得到应有关注。在只注意到嘉靖以后梁辰鱼、沈璟等南派曲家,而忽略薛论道、薛岗等北派曲家的情况下断言“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或谓”昆腔兴起以后”,“北曲则已成余响”,这就不免有些片面了。
任中敏先生作为现代散曲学之父,是我非常仰慕的曲学前辈。任先生的《散曲概论》是20世纪前期散曲通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故笔者多以任先生的观点和受其影响者的重要论著作为讨论依据,面世在任先生大著之后的曲学论著和文学史著作,在论及明代南北曲盛衰时,多接受任先生观点,转相祖述,大同小异,就略而不叙了。总之,笔者考察的结论是:在未有昆曲的正德、嘉靖以前,南曲早已盛于北曲;隆庆、万历以后,南曲成压倒优势,北曲进一步走向衰落,但曲坛却并非“只有南曲”,北曲也还没有成为“余响”,也更没有“消亡”。事实上,无论在曲家的案头,还是在歌几的口中,北曲不仅都还生存着,而且还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澄清这个事实以后,我们对明散曲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对明代南北曲的盛衰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文体的研究,无疑应当重新加以审视了。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