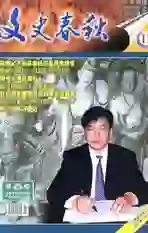项南父子的革命经历及寻亲轶事
2007-11-22孟昭庚
孟昭庚
曾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项南,以他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甚好的口碑。但他和他父亲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一段寻亲轶事,却鲜为人知。
项南的父亲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县,1925年在浙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项与年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的三马林达担任区分部书记,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团结发动华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对华工的残酷剥削,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4月,荷兰殖民主义者因“升国旗事件”大肆抓捕和屠杀华侨。项与年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关押半年之久后,被蛮横地驱逐出境。回国后,项与年被调入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在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以及搜集情报、惩治叛徒、营救干部。项与年曾和陈赓一道,积极组织并直接参加营救彭湃、杨殷,击毙叛徒白鑫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兄弟的行动。
一
1932年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项与年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任务主要是观察和了解敌人的动向,搜集军事情报。他通过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的莫雄先生,多次搜集、截获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事部署,派交通员冒死送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手中。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老同盟会会员和老国民党党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一度与蒋介石共事且私交颇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看清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嘴脸,便辞去军职在上海赋闲。在这期间,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的莫雄与中共上层人士交往甚密,曾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莫雄的这一要求。周恩来让李克农转告莫雄:“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要求参加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中央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入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暗中为中共地下党提供帮助。
1933年10月,蒋介石接受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任命莫雄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莫雄将计就计,暗中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商讨,由我党派人去司令部。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中共中央上海局接受了莫雄的意见,将党在上海的一批骨干派到江西,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任职。他们中除项与年外,还有保安副司令陈修爵、上校主任参谋卢志英(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解放前夕牺牲)、情报股长贾佐(希谊)等。项与年既是我党的情报交通员,又是保安司令部谍报组情报参谋。
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德安是南浔铁路中心点,按蒋介石的说法,是“赤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之一。为了迷惑敌人,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方面派人与当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联系,让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地方转移;另一方面让莫雄派出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并在“剿”共中,通过各种巧妙办法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这样不到6个月,“共匪”在德安地区“绝迹”了。蒋介石心中甚慰,给莫雄通报嘉奖。
二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此之前,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接受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策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推进,最后寻找红军决战。
在敌人新的进攻战略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集团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却脱离实际盲目鼓吹“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和敌人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指挥。
由于博古、李德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推向最后失败的境地。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进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会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通过电波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此事,而对党内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却秘而不宣。
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一个准备突围转移的公开信号,虽然红军总部尚未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在前方和后方悄悄进行了。
三
蒋介石和他的智囊团很快就捕捉到中共中央要放弃闽赣根据地向外“流窜”的信息和情报。这让蒋介石喜出望外,在他看来,消灭朱毛“赤匪”的机会就在眼前。他急忙于1934年10月初飞临庐山牯岭,召集南方五省军政首脑紧急军事会议,研究、讨论、拟定、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竭泽而渔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这个“计划”,彻底消灭中央苏区。
德安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按理还不够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但因他“剿共有方”,被蒋介石点名特邀参加。“铁桶围剿计划”决定动用150万大军,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等中央苏区根据地为目标,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的部署时间,待包围圈一经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然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就布上一层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精确到使火力能够相互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照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6个月进逼瑞金。到那时,瑞金周围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止红军突围,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并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其线路布置得十分详细,无一遗漏。
计划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指定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设置鹿砦,何处建弹药库、粮秣库、医院、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会议发给每位与会者的文件重达三四斤,内有“围剿”的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以及蒋介石的一系列“剿共”语录。每份文件上都标有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有序号。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便心急火燎地连夜赶往德安司令部。他冒着泄密杀头之罪,十万火急地向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研究。
四
情况万分紧急!蒋介石这个毒辣的计划一旦完成,中央苏区十几万红军和党政干部将劫数难逃。它事关共产党和红军的存亡,必须立即让党中央知道。项与年和战友们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的内容,密写到4本学生字典上。
鉴于项与年熟悉当地的人情和地貌,便由他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部、石城等8个县市,有几十道关卡,其中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难以想像。
当项与年带着抄有密件的字典混过几道关卡,抵达南昌时,想到后面的路途更为危险,他便拐进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找来几个信得过的地下党员,将密件缩写在薄纱布上,然后将它藏在鞋底。
为减少与敌人关卡的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的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憔悴消瘦,身体逐渐难支,走路已十分吃力。前面的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一大难题。经过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将自己的衣服跟一个山民调换,把一套又破又脏的褂裤穿在身上,然后以惊人的毅力,用石块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是一个身患重病的讨乞的疯老头子,浑身上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人见皆掩鼻而过。项与年就这样混过层层封锁线,用6天时间到达了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中央军委“三人团”的周恩来手中。
五
此时,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虽已决定转移,但在选择突围的时间和方向上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几天前已收到项与年等人由德安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感到形势十分危急,遂果断决定立即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除留下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斗争外,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失时机地指挥86万红军主力和后方机关,于10月中旬分别从瑞金以及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于都、会昌等地,一举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这时,距离蒋介石的庐山牯岭紧急军事会议闭幕还不到10天。“铁桶围剿计划”才开始贯彻布置,红军主力却突然突围而去,这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阵脚。
项与年这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前而又及时地突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项与年历经千难万险给中央送绝密情报,当时只有中央高层的几个决策者知道,毛泽东并不晓得。在长征途中,一次周恩来跟毛泽东谈及项与年时,毛泽东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
1956年国庆节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而冒杀身之险提供绝密情报的有功人士。为表彰他们为革命所立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中央军委之托,特请项与年专程到广州邀请莫雄先生赴首都出席国庆观礼。李克农代表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二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当然,这是后话了。
六
中共中央机关从瑞金撤出后,项与年又奉命去上海接受另一项特殊使命,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追剿军的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项与年火速赶回上海,和已接到电报通知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子华接上了头。刘子华把两名爆破队员带到上海大饭店介绍给项与年。为安全起见,刘子华故意对两名爆破队员说项与年是一位可靠的国民党朋友,这次是去南昌找差事干的,正好顺路带他们一下,到南昌后另外有人分配具体任务。
第二天,项与年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去南京。因一名爆破队员叛变投敌,项与年在南京被国民党密探拘捕转押到南昌。由于他始终沉着应付,一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拿出为掩护地下工作身份用的预备证件,证明自己是国民党员。在看管所里,他一再向敌人表白,并鸣冤叫屈,说这次去南昌是投奔朋友寻份差事的,根本不知道托他顺道带人到南昌的那个朋友是共产党。
好在那个叛徒对他的底细并不十分清楚,敌特机关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对他的看管也就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过赣江,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组织上考虑他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便于1935年初派他到香港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后来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姓更名为梁明德,先后在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事,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从事统战工作。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被调到陕西关中地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使他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妻子儿女身在何方、是生是死他一无所知。
七
当年,项与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时,朱、毛红军打到了闽西,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上安排工农通信社的交通员将他生活在闽西大山里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带到上海,用家庭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当时,项与年的儿子项崇德才10岁,在家乡列宁小学读了两年书。项与年想到,自己一旦被捕,敌人肯定会加害妻儿,便将儿子项崇德送到南京继续上学,托一老友照应。
项崇德在南京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6岁改名项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始到武汉,继到桂林。在李克农、廖承志的帮助和安排下,项南于1940年由香港辗转到苏北盐阜地区,在刚由河南竹沟经皖东抵达盐城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民运工作,20世纪40年代初任阜东县(今江苏滨海县)三坝区党委书记。
阜东三坝一带是笔者的故乡,直到现在,一些高龄老人还津津乐道60多年前那个才20出头的项教导员是如何的能干,如何发动他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组织他们参加民兵,用洋枪土炮保卫家乡的故事。
八
斗转星移,弹指一挥间,近20个年头过去了。革命胜利后,许多老同志或回到阔别的家乡看望久别的亲人,或通过组织寻找离散的骨肉,项南和他的父母都在相互寻找亲人,但找了几年都没有找到。这是因为项南和他的父亲在白区读书和工作时都改了名字,尤其是他的父亲不但改名还换了姓。
建国初期,担任东北人民政府监督委员会高级专员的梁明德隐隐约约听说儿子早已参加革命,不知在华东地区的哪一个省搞青年团工作。于是,他写信给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托他在华东一带寻找自己的儿子。
曾希圣四处打听,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任何线索,随后将此任务交给青年团省委书记项南,还特别嘱咐他把调查重点放在各级团委干部身上。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当时他只是感到惊讶:“咦,这位老革命梁明德的儿子的名字,怎么跟我的幼名相同呢!”但转念一想,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也没有向曾希圣进一步打探,问一问这梁明德是不是真名实姓,所以“稀里糊涂”地帮着找了一年,还是没有找到东北那位高级干部梁明德儿子的下落。
事有凑巧。一次,曾希圣率一个工作组下乡蹲点,搞农村互助合作调查,团省委书记项南也是工作组成员之一,正好与曾希圣同住在一户农家。晚上两人聊天时,曾希圣无意中发现项南颇像一个人,他想如果项南果真是梁明德失落多年的儿子,小时候就应该到过上海,于是便问项南:“你小时候去过上海没有?”
项南答道:“去过。”
曾希圣问:“还记得住在什么地方吗?”
项南答:“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住了两个月,便去南京念书了!”
“你父亲当时是干什么的?”
“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
项南的话引起了曾希圣的思考,便又问:“当时你年纪那么小,是谁将你从闽西带到上海的?”
项南说,是一个丝绸店老板,那个老板的小伙计只比我大5岁,记得路上他老讲故事给我听,还买好吃的地瓜干送给我。
项南这么一讲,曾希圣恍然大悟,当年正是他亲自安排那个“丝绸店老板”和那个“小伙计”将在上海购买的一批中央红军急需的无线电零部件,从上海乘船运至厦门港,然后进入闽西苏区龙岩镇,将物资交给红军物资转运站,再由他们负责运至红都瑞金。他还特别交待交通员,完成任务后顺道去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将项与年的妻小带至上海。
项与年在维尔蒙路将家安定之后,曾希圣常扮成一位姓胡的商人,到项家去谈“生意”。项与年那个聪明的儿子很讨人喜欢,每次见面总亲热地叫他“胡叔叔”,给他搬椅子、递烟。当然,他每次登门少不了要带一把糖果给他。
想到这里,曾希圣哈哈大笑,如释重负地对项南说:“你仔细看看,我像不像那个‘胡叔叔?”
项南猛然记起,脱口而出:“胡叔叔!”一把搂住曾希圣,热泪滂沱。
项南就这样找到了离散20多年的父亲。
九
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明德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见,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当时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工作。
再说当年红军长征后,上海地下党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项南的母亲与7岁的妹妹作为“匪属”,被国民党警察局关进提蓝桥监狱。在狱中,小妹背上长了一个毒瘤,由于得不到治疗,出狱时背已经直不起来。在南京读书的项南得知母亲出狱,特地赶到上海看望受尽牢狱之灾的母亲和小妹,和她们在照相馆合了一个影,就又赶回南京。哪知,这一次竟是他跟小妹的诀别。
项南的母亲出狱后,靠替人帮佣维持生活,由于经常遭到特务和地痞的恫吓和敲诈,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女儿回到闽西老家。土地革命期间,红军撤走后所分得的土地、房屋,又被地主老财拿了回去。母女生活无着,母亲更无钱给女儿治病,不久,不满8岁的女儿毒瘤发作,活活被疼死了,死的时候想喝一碗粥,可母亲连这一点要求都无法满足。
女儿死了,丈夫和儿子天各一方,杳无音信,而当年曾被苏维埃政府清算、斗争过的地主和白军的狗腿子见这个“共产婆”回来了,不但咒骂项家搞共产搞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还经常无事生非,借故找她麻烦,项母不得不离开老家,一个人在闽西大山里到处乞讨、流浪。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组织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闽西等地慰问当年曾舍生忘死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项南的母亲去慰问团打探丈夫和儿子,由于项南父子都改了名字,慰问团没人知道这两个人。但慰问团非常同情老区人民,凡是寻找在革命战争年代因参加革命而与亲人失散的人,都一一登记在册。
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回到上海后,将登记册印刷若干份,发给机关干部和华野部队团级以上干部,请了解情况的人提供线索,帮助老区人民寻找自己的亲人。
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机关工作的项南,就是从那份登记册上看到母亲王村玉的名字,才将贫病交加的母亲接出闽西深山的。
十
十年浩劫中,曾担任过辽宁省重工业厅厅长的梁明德,这位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战士、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竟被诬为“叛徒”、“特务”、“内奸”,遭受无休止的游街、批斗,被整得死去活来,受尽皮肉之苦和精神羞辱。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从此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但残酷的造反派并未轻饶老人,仍时常轮番审讯他、折磨他,最后又将老人押送至盘锦农场劳动改造。
饱经人世风霜的梁明德已到了风烛残年,不但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连个人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农场试图甩掉这个包袱,几经周折,查到了他儿子项南的所属单位——机械工业部。谁知此刻的项南也早已落难,被打成了“三反”分子,被押送农村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妻子则远在西北宁夏“五七”干校劳动,子女们也都上山下乡,天各一方。
一天,军代表找项南谈话,将盘锦农场“革委会”的公函交给他看,只见上面写道:“项南的父亲梁明德是叛徒,正在接受审查,因年高多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望动员项南接去赡养。”项南读后欲哭无泪,他没有想到革命一生的老父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军代表问项南如何打算,他只好强忍悲痛,如实相告:“我孤身一人自身难保,一切相信和依靠组织。”
不久,盘锦农场将梁明德遣送至原籍连城县农村。连城是革命老区,老区干部和群众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热烈迎接这位远方归来的革命战士,将他安排住进敬老院,为他治病。
1972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落实干部政策时,确认梁明德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决定给他平反,补发工资。赤诚的老人接到一大笔工资后,首先邮汇1500元给原单位补交党费,然后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改善交通。
在此之前,他曾拿出过去的积蓄,为本村购置一台发电机,使穷山沟里增添了光明。一天夜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许亚到连城检查工作,所到山区均一片漆黑,惟独途经朋口小镇,突然发现山村灯光闪烁,引人注目。随行干部告知:这是一位革命老人的无私奉献。许亚深受感动,执意下车拜访。交谈中,他意外得知老人的儿子项南竟是自己20世纪40年代在新四军的老战友。他敬佩这位饱经风霜的、为共和国立过汗马功劳的战友之父,当机立断,连夜派车把老人送往省城疗养院检查治疗。
十一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宣告结束,项氏父子的历史冤案双双获得解决。已入耄耋之年的梁明德虽重病缠身,但精神振奋,情绪饱满。此时,他的儿子项南也恢复了名誉,回到农业机械部担任领导职务,妻子和儿女们也相继从各地农村返回北京。
每当家人团聚,项南总是十分思念远在老家的父亲,他想把老人接来北京赡养,但进京户口难以解决。当时的户口关系到一个人粮、油、布、煤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于是项南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请求照顾,但被答复道:“你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你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大家都要求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那不是让组织上为难吗?”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噎得项南哭笑不得,从此不提此事。
1979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了解项南父亲的历史,更熟悉项南。一次开会时,他突然主动问项南:“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项南有口难言,只好如实相告。胡耀邦听后气愤地说了一声:“乱弹琴!”随即提笔写信,请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解决老人到京落户的一些具体问题。
福建龙岩地委立即把梁明德接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的肺炎,随即安排医院精心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待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到京。”
项南十分感激,当时他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工作极为繁忙。当项南率团走进机场等待登机时,突然接到父亲治疗无效病逝龙岩的电报。父亲晚年孤居家乡病逝,使项南极为悲伤,但出国考察事大,他只好委托妻子赶赴家乡料理丧事,而自己则准时登机赴国外考察。
鉴于梁明德曾为革命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委在沈阳为他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
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会堂上的横幅庄严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省委领导任仲夷、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亲临会场。许多人都不知道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道内情,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