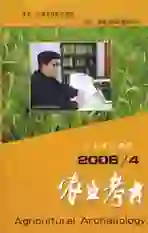生态环境与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活动
2006-11-24陈伟明戴云
陈伟明 戴 云
生产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也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产生的基础。而共同的生产生活地域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活动特点与特色。所以生态环境与民族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而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开发相对较晚的少数民族,在其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制约,有时更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探讨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了解历史时期华南各少数民族如何在一定的生态条件下,发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生产活动对于揭示生态环境与生产活动统一辩证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活动,长期以来,发展相对缓慢。除了受中原封建政权长期压迫歧视,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约束,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的结果。本来华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高温多雨,生物生长周期较短,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开发发展。但由于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峰峦叠起,也造成了降水或气温有较明显的差异,生态环境上也对农业开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华南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山区,更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广西隆林县德峨区,境内层峦叠嶂,连绵不绝,全区地形大都是海拔1300至1400公尺以上,十分之七八是石山,十分之一是半石山,只有十分之一是泥洼地。区内无川河流过,只能以小泉作灌溉。地势高,气候较冷,最高37度,最低零下4度,平均17度。(1)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彝族等少数民族,要发展农业,困难重重。同时,华南地区虽然降雨丰富,但岩溶地貌普遍发育,分布较广。岩溶地貌,水的渗透性较大,水土流失较快,易旱易涝,容易造成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多的限制。如近代广西南丹县拉易乡,地处山区,由石灰岩构成的高山,盘亘在全乡境内。田坝多被高山包围,山谷小溪没有出口,只靠一些大大小小的岩洞来宣泄,水灾旱灾由此而来。如遇大雨,山洪立即暴发,消水洞便宣泄不及。而这种消水洞又往往与地下伏流贯通,有时洪水过大,伏流也同时涌涨,平日的消水洞不仅不起宣泄作用,反而涌出伏流。这样一来,田坝顿成泽国。如果天雨不歇,禾苗经过一昼夜以上的淹没,往往被水泡死。即或不然,那些由洪水带来的泥沙,沉淀在田里,如淤积过厚,也要把禾苗压倒而逐渐霉烂。有些消水洞纡曲狭窄,往往为山洪夹来的草木所壅塞,以致宣泄不畅,也会造成涝灾。(2)给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带来许多不利的因素。历史时期的华南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偏僻山地,山高坡陡,耕地零散,森林遍布,环境封闭,农业生产要能够真正开发,社会与自然的条件,都不可能给历史时期的华南少数民族,带来更多的优势。首先,少数民族地广山多,人烟稀少,令历史时期华南各少数民族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低效益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没有象汉族发达地区在较小地域范围内承受较大的人口压力,具有进行复种轮作集约经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对于提高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缺乏迫切感。其次,山陵起伏,森林蔽日,一方面固然给农业带来一定的困难。如清代桂林地区,“清湘间山深水阔,可耕而庐者,十无二三。凡为生非渔则樵。”(3)而另一方面,江河密林,蕴藏着丰富的山珍海味,鱼鳖野兽,也可成为人类重要的天然食库,也使华南各少数民族,能够以较为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渔猎、采集等经济,能够长期与农业生产并存,并在较大程度上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令人感受不到农业生产带来的压力与压迫感。因此,华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他们可以较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形式与技术,维持其基本的食物来源,缺乏农业开发的真正动力,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盬饶食,无饥馑之患。”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发展特点。台湾地区气候湿热,山高林密,杂种丛生,易于收获。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生计提供了重要的动植物资源,也使台湾少数民族长期感受不到主粮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压力。对农业生产的开发缺乏紧迫感,使之能够以较为原始落后的生产形式,如刀耕火种、渔猎经济就可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与需求。有谓:“熟番种植多于园地,所种悉旱稻、白豆、绿豆、番薯,又有香米,形口长大,味甘气馥,每岁种植,止供自食,价值虽数倍不售也。……内山生番,五谷绝少,斫树燔根,止种芋魁,大者七八斤,贮以为粮。”(4)又“台湾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周围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栖而不火食者,无所求于中国。”(5)缺乏农业压力,也必然没有农业开发之动力,说明了历史时期,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农业开发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华南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再次自然地理环境隔绝,也令华南少数民族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缺乏更多生产技术及文化的交流吸收。广西庆远府山区,曾有民谣谓:“铁锁炼孤舟,千年永不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6)这必然为某一地区,某一民族长期保持某种生产方式提供温床。如海南黎族一些地区,直至清代,仍然“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7)与华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尽管在汉族移民的推动下,农业生产有了相对较大的进步,但由于台湾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普遍起点较低,始终未能扭转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总是不断自我调节,自我适应生态环境,形成自己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直到清中后期,生态环境仍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带来深刻的影响,台湾少数民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仍然相当有限。如台湾彰化县,“蓬山八社所属地,横亘二百余里,高阜居多,低下处少,番民择沃土可耕者,种芝麻黍芋,余为鹿场,或任抛荒,不容汉人耕种。”(8)又如西势社番者,“不谙岁次,以花开纪四时,打牲为恒业,间有汉人教之耕种稻谷,以为宝贵,以短刀代犁锄,并无牛只。”(9)历史时期整个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为低,常常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制约,农业生产普遍处于较为缓慢的历史状况,主要表现在下述若干方面。
1、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农耕民族中,实际上都可能长期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只是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各地区各民族历史时期所经历过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其内涵或有区别。有些可能只是开垦山林为耕地,属于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如中原汉族远古时期就曾实行过类似的形式,即《盐铁论》所称“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而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则采取游耕的方式。而且中原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向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化。而历史时期华南各少数民族,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则长期保持类似的生产方式。宋代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资蓄虚乏,刀耕火种以为猴粮。”(10)如宾州地区,“澄江洞,在迁江县之西,瑶人所居,无田可耕,惟恃山畲,刀耕火种,造楮为业。”(11)直至明清时期,在边远山区聚居的华南少数民族,其生产方式仍无多大转变。广西向武瑶,“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稻田无几,耕种水芋山薯以助食。”(12)又山子,“斫山种畲,或冶陶瓠为活,田而不粪不晓,火耕,耕一二年视地利尽辄迁徒去。”(13)海南黎族也是如此,其“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逾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盖天所以制其力也。”(14)台湾地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刀耕火种,据调查,台湾少数民族开垦就是将处女地砍去草木,纵焚以火,将需要的地面,整理清楚,以便耕作。(15)可知历史时期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形式具有普遍性与长期性,无论是粤北、粤东,或是桂北、桂西,或是海南台湾,无论是壮族瑶族,还是黎族、高山族,都曾进行了类似的生产活动。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刀耕火种生产方式,适合在山林地貌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这正是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重要的聚居区域。近代民族调查也说明了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与长期性。广西富川县富阳区瑶族,每年4月下旬,就利用刀斧工具砍山开田,砍山以后的半个月,烧山治田以种植粮食。(16)又环江县玉环乡毛难族,一般新开的荒地,仍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即把山林树木砍倒烧光之后,把米撒下,拔草一二次,就等收成。(17)这也是生态环境所致,华南地区少数民族不得不长期保持刀耕火种形式。如广西南丹县拉易乡,小米的栽种,还是刀耕火种的方法进行。这种耕作方法,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其法:在长满荆棘、藤蔓、芒草、小竹木的石山上,选择一片有或大或小洼坑而稍有泥土的地方,先将草木砍尽,晒干后,放火烧焚,趁着灰烬还热的时候,立即撒播种子(灰冷后则种子发芽率甚低,且成长亦不良好),不须挖地翻土。经过二十天左右,地上野草(特别是芒草)复发新苗,因撒播株间甚密,不能用锄刮中耕除草,必须用手去拔,草少的拔一次,多的则须拔二次。当地称这种方法为“砍火焰”,砍火焰只能撒种小米一年,第二年必须把地丢去,如果地好,也须另行挖土,换种别种作物。过去耕种水田较多是壮族,极少人搞这种活路,只有外地迁入的汉族、苗族,由于多是住在石山岭上,水田缺乏,才不得不多砍火焰来种粮食。(18)华南地区山多平原小,丘陵交错其间,岩溶地貌发达,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生活的少数民族,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生产形式维持生计。所以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普遍长期刀耕火种,绝非偶然,生态环境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也由于刀耕火种主要是在崎岖山地中披荆斩棘,劳动强度较大,收益较低,也必须以群体游耕方式,才能有效持续地开展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
由于华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其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具有举族耕作或游移耕作的特点,因为华南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边远山区,以山为耕,石多土小,劳动强度较大,要开垦山地,非举族共同开发,集体劳动不可。如海南地区,明人有谓:“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虽绝顶亦可耕植。黎俗四五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林,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皓洌,则纵火自上而下,大火烧尽成灰,山下尺余且熟透矣。”(19)另外,人食无尽,地力贫瘠,产出有限,只好实行游耕方式。清雍正年间,有载:“粤西省田少山多,其山可以布种者杂粮竹木,罔不随地之宜以尽利,乃有一等不毛之山,顽石碩确,动辄绵亘数十百里。既已农力之难施,苦材产之有限。”(20)在这种生态环境条件下,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为低下的华南各少数民族,游耕方式乃是最好的选择。有谓:“谣人,其在南粤者,在在有之。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徒。”(21)当然,也有经过较长的时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生机,迁回原刀耕火种之地,继续进行类似的生产活动。海南有苗黎,“不耕平地,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一年一徒,峰茂复归。”(22)以游耕蓄养地力的自然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因地制宜之计。而且华南区域,各地自然生态环境或有差异,也会导致类似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特点。如台湾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与华南内陆一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其生产方式大体一致,一般也是把山林草地上的草木砍去,纵火焚烧,再进行简单的农耕种植,在一块土地上刀耕火种一段时间后,地力衰退,便易地游耕。但也呈现了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游耕周期的不同,台湾地区相对华南其它地区为长。据近代民族田野调查,台湾瑞岩地区的烧烟农业的一个特征就是轮作,这里所指的轮作不仅是在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时间种不同的植物,而是在一块土地上,利用了相当的年限,其土质瘦瘠,乃易地耕种,让这块土地复又长满杂草,将来再焚烧开垦。他们的耕地,处女地可种十至十二年,第一轮的轮作地则可耕六至八年,其后依次递减。(23)这主要与台湾地区的土壤情况较为优质,地力保持良好的生态状况有关。有谓:“台地黑壤,甚肥沃,不须下粪,布种自二三月至九十月,收获亦如之。”(24)可知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影响。
2、粗放农业
粗放农业,是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长期保持的又一重要生产方式。粗放农业主要表现为粗种薄收,受自然生态因素制约影响的程度较大,它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比较,至少从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来看,应该是有较大的进步,也应该进进入了定居农业阶段。但是一般来说,粗放农业生产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种植技术简单粗糙。如缺乏有规律的农业生产时令气节,如海南地区,史称:“黎内不记年月,无令节,有黎人来者问其年若干岁,茫如也。然耕作获利颇与四时气节不爽毫发云。”(25)又台湾少数民族,有谓:“番人无姓氏,不知岁月,惟凭草木,听鸟音以节耕作。”(26)其农业生产似有较大的偶然性与随意性,保持了较为浓厚的原始色彩,对农业生产没有进行规律性的探索总结。而一般农业生产技术也较为简化。在一些山区或条件较差的地区,其农业种植杂乱无章,随种随收,听天由命。如宋代钦州,“田家卤莽,牛耕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地。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27)明清时期,广西地区壮人,有谓:“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家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每岁二月布种毕,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播于田,更不复顾,遇无水方往缺灌,略不施耘荡锄之工,惟耨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耨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获,每一亩得谷者二石者为上。此亦习于逸惰而不力耳。又有畲禾,乃旱地可耕,彼人无田之家并瑶僮人皆从山岭上种此禾,亦不施多工,亦惟耨草而已,获亦不减水田。彼又不知种麦之法,故膏腴之地,皆一望芜芥不顾。”(28)雍正二年,“自柳达桂,沿途见弃地颇多。”其中“山奚谷险峻,瑶僮杂处,其间所垦之田与村庄稍远便虑成熟之后被人盗割,徒劳工费,一也。民性朴愚,但取滨江水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之术,二也。不得高阜所宜杂粮之种,三也。不易各省深耕易耨之法,四也。”(29)又海南黎族,有谡:“黎人耕田,不知用犁起土,以水牛四五头至六七头乱踹田中,使草入泥,泥涌草上,平之以栽秧。”(30)直至民国初年,其农业生产尚为粗糙,仍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有载:“陆稻即旱稻,凡无水之田,或山坡干亢之地,均适于栽杆。居山小部落之黎人及一般苗人,则多种此。播种与水稻无异,惟分秧时用锄锹掘穴栽之。间有焚去山坡之自然草木,就地播种,不再分秧,任其生长者,各山僻地均有见之。”(31)又台湾地区,北路内优诸社少数民族,“垒繴深溪,树木蓊翳,平原绝少,山尽沙石;种黍秫、薯芋,俱于石罅凿孔,栽植黍秫,熟留以做酒。”(32)又“生番人稀土旷,地无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随意树艺,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余粮胜食。”(33)可知,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尽管社会发展程度或有高低,但普遍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耕作种植法。
华南地区粗放农业生产方式的长期延续,除以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了民族群体社会进程发展缓慢。生态环境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华南生态自然环境,限制了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与发展,劳动生产率低下,影响了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渡。如宋代广西静江地区,常以踏犁作为主要的耕作工具。而当时的广南西路并不缺乏耕牛。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十载,隆兴元年,有人曾提议“请权往广西马纲三年专令市牛,盖广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贱。”但是无法在岭南山区大规模推行当时颇为先进的牛耕之法。即使宋代广西农业较为发达的静江府也受制于生态环境,而以踏犁为主要耕作工具。踏犁是一种以人力翻土的农业工具。有谓:“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钅矍耕之功则倍。”(34)可知踏犁比牛耕的生产效率要低。据专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保存下来的踏犁进行考察的结果,其特征一方面保留了耒耜的遗制,另一方面又套有铁制刃具,证实了踏犁是一种较进步的人力翻地工具。(35)至于宋代静江地区使用踏犁,宋人有详细的说明。“静江民颇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长六尺许,末施横木一尺余,此两手所提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可耕三尺,则释左脚而以两手翻泥,谓之一进,迤逦而前,泥垅悉成行列,不异牛耕。予曾料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问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曾喂饲,夏则放之水中,冬则藏之岩穴,初无栏屋,以御风雨。……南中养牛若此,安得而长用之哉。若夫无牛之处,则踏犁之法胡可废也。又广人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两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木莽巨根,无不翻举,甚易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36)可见宋代广西静江地区使用踏犁,有时乃与耕牛配合使用,原因是静江地区多山地丘陵,且新开发地区荆棘丛生,使用踏犁较之牛耕更为方便实用。如与踏犁有异曲同工的起土工具锋,“古农器也,其金比犁叫《加锐,其柄如耒,首如刃锋,故名锋,取其钅舌利也。”宋元时期,“若地坚恪,锋而后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37)又现代贵族三都县水族人民,耕牛很多,犁耕盛行,但仍十分热衷于使用踏犁,主要是由于踏犁轻巧省力,制作简易,实际功率又远非手执锄头可比。特别是在耕地不平的山地,据称破土角度远比犁耕转动灵活。(38)近代广西正万乡瑶族,所使用的手犁,也是类似宋代踏犁,它适用在斜度很大或混有很多大石的畲地,工作效率很低,但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下,不得不使用类似的踏犁工具,故又称为脚踏犁。(39)可见华南地区少数民族使用踏犁,并非不知牛耕,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生态环境所致,古今如是。如海南黎族,有些地区,“春耕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40)又崖州抱寨峒,“有水田数十亩,耕时仅以牛蹂,即行播种。”(41)表面似乎也是不懂牛耕之法,但实际上也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如昌化县东北,“黎歧以刀耕火种为名,曰斫山。西南浮沙荡溢,垦为田,必用牛力蹂践,令其坚实,方可注水。”(42)所以华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常常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导致生产工具改进缓慢,劳动效率低下。近代民族田野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广西隆林县彝族,锄头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由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山地石头多草多,锄头也显示了适应山区特点,柄轻短小,便于携带。(43)又广西茶山瑶所用耙,绝大部分是木制,其构造形式,则完全与汉壮地区的相同。这种木耙,除铁箍外,本族都能自制,耙身耙齿,都用当地所产的一种木质坚韧的黄桑木制成。用木耙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山田田底多石崖,铁齿耙反易损坏,而不如木齿耙经久耐用。第二是木质木耙本身轻巧,耕牛容易拖拉。第三是木质就地取材,并可自制,即使损坏也容易修理或制造而不费多大成本。第四是山内大多数是水源充足的淹冬田,田泥久经水浸,十分融软,木耙也尽可能把它耙碎,用不着多费银钱购制铁耙。(44)广西南丹白锹也有自己特点,木柄与锄嘴不在一直线上面,而约呈30度角,据说这是更便于山坡操作的缘故。(45)虽然生产工具适应了生态环境的需要与条件,但也限制了生产工具的发展改进,从而延续了粗放农业生产的长期存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以简陋生产工具从事粗放农业,台湾北路少数民族,“耕用小锄,短刀掘地而种,或将坚木炙火为凿,以代农器,近亦有驱牛用犁耙者。”(46)由于生态环境的特点,导致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工具难以进行较大程度的改进。因此,进行低效率的粗放农业生产活动,便成为华南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下的主要生产方式。直至近代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农业生产方式。据田野调查报告,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甘长乡,山区鸟兽危害大,种下的种子容易被挖出吃掉,因此瑶族人民使用削尖的木棒打洞放下种子,然后再用脚踩,盖上泥土,鸟兽不易发现,免于受害。播种时,男人在前打洞,妇女在后放种子,随即用脚一踩就算完事,这种方法速度极慢,一般两人一天能播三斤种子,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47)
华南地区生态环境,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造成了农业工具的简陋与改进缓慢,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要种植具有较高技术要求的农作物,显然存在较大的困难。即有种植,要取得较好的收成,也为不易。所以粗放农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种植杂粮及根茎类植物为主。因为类似的作物粗生易长,可以在较为落后的地区或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种植,并取得一定的收成,与粗放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华南地区,虽然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但由于华南地区的地貌状况复杂,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条件更是恶劣,水利灌溉设施落后。粤西地区,“水田低称田,旱田高则称地,田皆种稻,地种杂粮间有种旱禾,雨水足即丰收,谓之靠天田。”(48)如百色地区,“农业岁一稔,四月莳秧,九月割稻。以余暇负贩营生,搏蝇头利。其地多山少田,且无水利,十日不雨立槁,一月不雨水就涸。”(49)农业生产难以保障。或有依靠简单的水利工具或设施,进行水利灌溉,显示了较低的农田水利灌溉水平。西林瑶,“散处林谷,所种山稻、子、野芋,待雨而耕,旱则移就泉源,疏沟架槽,引以灌溉,终年一收,擒禽兽为食。”(50)或有所种山田,“必待雨而耕,旱则竹笕引泉以灌。”(51)农业生产要进一步向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过渡,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农作物优化选择也受到较大的局限。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制约了农作物生产种类的选择与扩大。台湾地处热带亚热带,湿热多雨,应较适宜种植水稻。但是在台湾少数民族的主粮生产中,水稻种植相对较少,而旱稻及其他杂粮的种植较为普遍。这也是受台湾水文生态条件的限制所致。有谓:“台地溪泉大者数十,小者无算,何以溪道迂浅,故水发则有泛滥四溢,冲缺田禾之患,不设堤闸,故急泻于海,则有灌溉无资之虞,是宜浚之。使得多开旁支,节其高下,以引致田间筑堤以蓄之,开门以泄之,则可以资灌溉之利,可以杜冲缺之患,水为利而不为害,无水旱之虞。”(52)而台湾少数民族,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力有限。如台东州,“所有溪河,皆两山夹之,所有番社、民庄,皆在山之麓,水之滨,所有荒地,皆溪中沙滩稍高之处,稍挂于泥,草生甚茂也,弃而不开,恐有水患也。所有已开高地,皆在近山远溪流之处。然亦难免于水患,以山甚陡峻,水易涨且猛而暴也。”(53)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增大了台湾地区水利工程建设的难度。台湾地区虽然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受地貌地形的影响,河溪流程短,落差大,一旦台风暴雨来临,溪河容积有限,或造成水土流失,或造成洪水泛滥,淹没农田。而主要聚居于山地的台湾少数民族,难以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也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645年3月,据外国人记载:“台湾之土地大多肥沃,适合栽植各种作物,糖之产量相当多,稻则不栽种于水田而植于旱田,因此产量少,又出产小麦、大麦、豆类、棉、麻、烟草、蓝、菜种、生姜等,但各种均产量不多,只与播种之种子同量而已。”(54)其“一筹水利,番民农事多不讲求。”(55)实际上也是无能为力。这样水稻种植反而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以种植杂粮为主。所以在生态环境的制约下,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困难重重,唯有以种植一些要求较低的农作物,以适应环境的制约,进行粗放农业生产。宋代广西地区,“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56)又明清海南地区,“地高田少处,则种山禾或薯芋、天南星、粟豆,兼粒食食之。”(57)清代粤西,“上林下旺各就其地所产,大概相同,自粳稻外,惟包粟、山薯及芋,四月莳,九月获,入冬间种荞麦。”(58)仍然是以种植杂粮及根茎作物为主。类似的杂粮作物,对土地质素要求不高,適合华南地区土壤肥力不足的条件。清代瑶民,“傍山皆硗确,稻谷不生,只宜高粱、荞麦,日猎野牲以供厨。”(59)又“田州土瘠,多种芋粟为饔飨。”(60)而且杂粮种植,水利技术与种植技术要求不高,一般无需较精细的田间管理,适合山区落后的生产方式,甚至可以游耕的方式维持生产。正如明人王临亨《粤剑编》卷二所载:“瑶民处深山之中,居无栋宇,以芒为命,芒似芋,遍山种之,食一山尽,复往一山,与北虏之逐水草驻牧者相类。”可见,华南地区少数民族粗放农业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3、渔猎采集
华南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低下,且多聚居山区恶劣环境。因此主粮与主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供不应求。唯有靠山食山,靠海食海,以渔猎采集经济,作为主粮生产与主食消费的重要途径与补充,历久不衰,成为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重要的生产形态。如宋代抚水州,“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口,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徒他处,无羊马桑柘。”(61)明代南宋地区瑶人,“种植禾豆、山芋,杂以为粮,截竹筒为炊,暇则取山兽以续食。”(62)或有以采集经济为主要生计。清怀远苗人,“山产桐茶树,以其子为油,以资生计,贫者或以采薪为业。”(63)又伶人,“生广西奥谷之中,状如猩狒,不室而处,饥食橡实百虫。”(64)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也表现了类似的特点。据载:“台北未入版图之前,惟以射猎为主,名曰出草,至今尚沿其俗。十龄以上,即令演弓矢,练习既熟,三四十步外,取的必中。当春深草茂,则邀集社众,各持器械,带猎犬逐之,呼噪四面围猎,得鹿则刺喉吮其血,或擒兔生啖之,腌其脏腑令生蛆,名曰肉笋,以为美馔,其皮则以易汉人盐米烟布等物。”(65)又台湾噶玛兰地区,“诸番耕种田园,不知盖藏,人各一田,仅资口食,割获连穗,悬之室中,旋舂旋煮,仍以镖鱼打鹿为生,其耕不知时候,惟视群木萌芽为准。”(66)反映了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渔猎经济所具有的长期性与普遍性,而且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
其一,华南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其渔猎经济,除了个别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普遍与粗放农业相结合,在古代中后期尤其是这样。如东莞县瑶,“邑至六七都,无物产,土瘠人穷,岁一种稻即止,田事之余,搏鹿射虎,捕逐鹧鸪、狐狸,与艾黎杂居。”(67)又西林土人,“散处山林,架木为屋,寝其上,牛畜其下,遇水则种植于山巅,而引以灌溉,终岁一收,闲则猎较。”(68)又台湾北路诸罗番,“崩山八社所属地,横亘二百余里,高阜居多,低下处少。番民择沃土可耕者,种芝麻、黍、芋余为鹿场,或任抛荒,不容汉人耕种。”(69)可知,直至明清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渔猎经济,虽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并没有支配整个经济生活,常常与粗放农业互为表里,互为补充。除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渔猎采集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也是自然生态环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反映。华南少数民族虽然长期保持渔猎采集生产形态,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促使他们必须与粗放或原始农业相结合。因为据有关研究表明,热带亚热带生态环境及是地球上变异最多、内容最复杂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以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古代华南地区,有较大面积的热带亚热带雨林,林木茂盛,植物种属极多,而相对而言,动物种类较少。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地区,其动物和植物的比例远远低于地球其它陆上生态环境。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动物种类之中,也是非脊椎动物占优势。而其中的脊椎动物,也习惯于单独活动或者以小家庭为单位的活动,不利于人类狩猎经济的单身发展,对食物原料的开发则有相当大的限制。所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对自然生态环境认识与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由森林山地移居河傍低地台地,以渔猎采集经济结合原始或粗放农业经济而发展,乃势所必然。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汉族农耕技术日渐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华南少数民族要继续保持单一的渔猎经济,既没有出路,也不可行。因为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开发的不断加强持续,其封闭性和原始性逐渐减弱,野生动植物资源也会日渐减少。一旦生态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单一的渔猎采集经济模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而逐步走向与粗放农业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如乾隆二十八年,“昔年,近山土番鹿场,今则汉人垦种,极目良田,遂多于内山捕鹿。”“鹿亦渐少。”(70)渔猎采集经济的衰退,除了社会文明风气不断开化外,也与生态环境的演变息息相关。华南少数民族从远古单一渔猎采集经济,逐步走向与粗放农业经济结合,正是生态环境与社会条件变化的重要反映。
其二,除了生产专业性较强的少数民族,其它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狩猎与捕鱼活动密不可分,同步进行。华南地区,山陵起伏,河溪纵横,即使聚居山区的少数民放,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可供利用。他们常常因地制宜,把陆上狩猎与河溪捕鱼同步结合,均衡并重。宋代山瑶,虽以刀耕野猎为主,但同时也以各种方法,利用河溪食物资源。有谓:“山瑶无渔具,上下断其水,揉寥叶困鱼,鱼以辣出,名痨鱼。”(71)又海南黎族,“深山多恶兽,能伤人,黎人每出门,必带弓箭,佩小刀,所以为防也。其弓屈木为弓巴,剖藤为弦,箭用竹为之,铁簇无羽,弓短而劲,箭利而准。小刀连靶尺许,用木挖空贮。黎歧无不能射者,射必中,中可立死,每于溪边伺鱼之出入,射而取之以为食,其获较网罟为尤捷云。”(72)说明了渔猎经济的密切性。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渔猎不分,同步进行。噶玛兰地区,“兰地未入版图以前,诸番惟以射鹿镖鱼为生。”(73)台湾地区河溪,常夹杂于山谷丘陵之中,山水相连,渔猎生态环境合一。如台湾北路新港诸社,“凡捕鱼于水清处,见鱼发发,用三叉镖射之,或手网取之,小鱼熟食,大则腌食,不剖鱼腹,就鱼口纳盐,藏瓮中,俟年余生食之。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寻,获鹿即剥割,群聚而饮,脏腑腌藏瓮中,名曰膏蚌鲑,余肉交通事贸易纳饷。”(74)其生产方式也是渔猎结合,台湾河流短急,又穿流于山丛之中,水土保持良好,污染程度较低,河流清澈见底,也为台湾少数民族的捕鱼活动提供了方便。由于渔猎同一,一些生产工具,实际上已兼备狩猎捕鱼之功能。有谓:“社番颇精于射,又善用镖枪,上簇两刃,杆长四尺余,十余步取物如携。曾集社众,操镖挟矢,循水畔窥游,鱼口佥口句浮沫,或扬兑肺玻辄射之,应手而得,无虚发,便生口敢之,腌渍则反取微臭者以为佳。”(75)实际上也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得天独厚,为华南少数民族提供陆上水上的生物资源。这样渔猎结合,便成为华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生产特点。
其三,由于华南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森林密布,江河纵横,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如海南琼康山,俗名琼皑山,在县南二百七十余里,“有苗人居山下,横直二十余里,高数十仞,林木荫翳,有香木、虫丝、艾粉、红藤、薯莨诸木,并麋鹿、獐猿、山猪诸兽,利产甚巨。琼定二属,均赖其利。”(76)也令华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捕猎,有时也表现了规模庞大,获利丰厚的围猎特点。如明代海南黎族,“黎族二月、十月则出猎。当其时,各峒首会,遣一人二人赴官告知,会但出每数十村,会留壮兵一二十辈守舍,男妇齐行。有司官兵及商贾并不得入,入者为之犯禁,用大木枷茎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顾,何其愚也。猎守,土舍峒首为主,聚会千余兵,携网百数番,带犬数百只,遇一高大山岭,随遣人周遭伐木开道,遇野兽通行熟路,施之以网,更参置弓箭熟闲之人与犬共守之。摆列既成,人犬齐备叫闹,山谷应声,兽惊怖,向深岭藏伏。俟其定时,持铁炮一二百,犬几百只,密向大岭,举炮发喊,纵犬搜捕,山甚震动。兽惊走下山,无不着网中箭,肉则归于众,皮则归于土官,上者为麇,次者为鹿皮,再次者为山马皮,山猪食肉而已,文豹则间得之也。”(77)其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猎物丰富。可见其渔猎生产规模之大,这也是与生态环境中所蕴藏的丰富生物资源有直接关系,特别是那些森林植被保存比较好的地区,其猎物也相对较为丰富。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其渔猎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据载:“当春深,鹿场高丈余,一望不知际,四围先掘火坑,以防延烧,逐鹿因风所向,三面纵火焚烧,前留一面,各番引矢镖枪齐发,围绕擒杀,鹿积如丘陵。”(78)说明了华南地区生态环境所具有丰富的狩猎资源,一些地区需要较大规模的合力围捕,方能有效地开发利用狩猎资源。
从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上述三种主要的生产形态发展可以看到,生态环境对生产形态的形成、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长期遭受封建政权民族压迫剥削的少数民族而言,生态环境的因素,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
首先,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农业开发的规模与水平。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的民族,其改造影响生态环境的能力则越弱,受生态环境因素制约影响也越大。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农业开发长期缓慢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华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处于山陵起伏地带,岩溶广布,石多土少,耕地分散,易旱易涝,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土壤肥力持续性差,对农耕极为不利。要改造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难度。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或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环境。而当生产力发展尚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阶段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只能较为被动适应生态环境的制约,以较简陋的工具,开展有限度的农业生产开发活动,劳动效率与劳动效益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据田野调查,近代广西凌乐县后龙山瑶族,工具中主要是扁锄,长二寸,宽一寸多,是几百年来主要的工具,几种作物都要利用它,如除草、培土、挖土、挖红薯等。据传说百多年前,后龙山上还要木宪木削尖来作犁头用,或是用尖木在石头山上,当作锄松土。(79)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生态自然条件,对某些生产特点特色的形成也带来重要的影响,从而在生产民俗上也体现了地方民族特色。如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粮食贮存,或许也是一个典型。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盛行的粮食贮存方法,通常是连作物秆一齐保存。宋代,“静江民间获禾,取禾心一茎藁,连穗收之,谓之清冷禾,屋角为大木槽,将食时,取禾椿于槽中,其声如僧寺之木鱼,女伴以意运杵成音韵,名曰椿堂。每旦及目昃,则椿堂之声,四闻可听。”(80)清代海南,“黎人不贮谷,收获后连禾穗贮之,陆续取而悬之灶上,用灶烟熏透,日计所食之数,摘取煮食,破颇以为便。”(81)广西思恩府,“僮禾,各州县及土属所出,颗粒大而食味长,九十月收获,连草逐茎摘之盈杷,终岁不脱。”(82)类似的贮存方式,大概是与华南地区湿热多雨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因为粮食贮存,一般需要通风干爽场地。由于华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技术普遍落后,游耕色彩浓厚,粮食贮存,既缺乏良好的场地,也难以具有较好的貯存设施及较高的贮存技术。把粮食果实连秆保存,或可处长粮食的贮存期,悬于灶上,自然干燥通风,可起到防潮防霉的保护作用。久而沿之,便成为华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的又一重要特色。近代民族学材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西西林县瑶族,旱谷成熟时收割,旱谷刚收下时不能当时脱粒,要等若干时日后,待其干后,才能用木棒将谷粒从穗脱下,故收获时,不能用镰刀或锯镰割切,而用禾剪将谷穗连同约一尺之长禾杆一起剪下,捆扎成把,产量也是以把计算。(83)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土壤、植被及气候等自然条件,这些都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尚为有限之时,生态环境因素往往有可能成为主导,对民族生产的发展方向、方式以及生产内容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某一个特区或某一个民族的农业生产特点与特色。
其次,华南生态环境也为少数民族的粗放农业或渔猎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与持续性。历史时期的华南地区,山高林密,植被茂盛,杂草丛生,蛇兽出没。如新石器时代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就是处在一个多水的有小型湖沼分布山间盆地之中,近处的山丘,生长了浓密的灌丛,远处的山区,大概是原始森林的茂密地带。甑皮岩中的动物群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热带亚热带的现生种类,更接近于现在西双版纳或更南地区的气候。(84)这一植被状况直至明清时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仍没有多大改变。清人有谓:“粤故多猿,予自二禺至英德,自氵光口以至连阳,自石峡又至东安,自六泷以至郴口,一路高峰绝,崖谷连绵,古木蔽天,百里阴黑失天日,群猿聚族其间,节节相应,恻恻忄妻忄妻。”(85)雍正三年,广西左江地区,“地方千里,深山密森,多人迹不到之处。”(86)又“镇安沿边,与安南接壤处,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树,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郁者,其地冬不落叶,每风来万叶皆碪,如山之鳞甲,全身皆劲,真奇观也。余曾名之曰树海,作歌记之。其下阴翳,殆终古不见天日,故虺蛇之类最毒。”(87)可见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其生态环境很多尚处于原生自然状态,为渔猎采集经济形态提供了条件。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清初,台湾西部地区还分布着广大的热带森林草丛母,“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复劲,弱者蔽肩,车弛其中,如在地底。”(88)又“台湾多荒土来眡,草深五六尺,一望千里,草中多藏巨蛇,人不能见。”(89)天然生态植被仍处于原始状态。另一方面,在台湾生态环境的生物链中,大型肉食动物较为少见,也为适合人类捕猎的小型个体野生动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可能。据载,台湾地区,“山无虎,但有豹,但不噬人,故鹿、麝、獐、麂之属,成群遍野,莫为之害。”(90)有利于为人类保存大量的渔猎资源,为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生产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温床。而且山区地形复杂,刀耕火种,只能粗放经营,杂种薄收。清代泗城府,“地鲜平畴,土人皆凿山以耕,导泉引涧,功劳而收薄。”(91)特别是华南山区,水利工程建设长期落后,要开展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以粗放农业维持生计。如雍正年间,柳州桂林地区,“山溪险峻,瑶僮杂处”,“民情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之术也。”“高卑所宜杂粮之种也。”(92)特别是华南一些地区,土壤条件尚好,以粗放农业生产也可有一定的收成,维持民族群体生计,如海南地区,“黎内多崇山峻岭,少平夷之地,然依山涧为田,脉厚为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其米粒大色白,味颇香米,然外间人食之多生胀满,琼人所谓大头米,即黎米也。”(93)台湾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较为肥沃,作物易生易长,粗放农业生产与收成,也能够满足消费。有谓:“台地土壤肥沃,田不资粪,种植后听之自生,不事耕耘,坐享其成,倍于中土。”(94)也导致台湾少数民族缺乏农业生产技术的积极性。“且所垦既多,田不耕籽,但知广种薄收,不知深耕易耨,农工之惰,亦由是焉。”(95)类似的生态环境,令少数民族能以较低的生产水平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就能满足要求不高的生活消费水平,从而能够长期维持粗放农业与渔猎采集经济等生产形态。
再次,生态环境也可能给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生产带来了不稳定性。由于生态环境封闭复杂,华南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其农业经济往往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如海南琼州,“东界田不及西界田,……。东田瘠虽粪,至有用骨者,然皆望天,不事桔槔。”(96)靠天吃饭,只能听天由命。而自然环境变化无常,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渔猎采集经济一直长期保存,正是为了农业生产不稳定时能够维持民族生计。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台湾生态环境也使台湾少数民族的粗放农业经济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台湾地处台风带,风灾频繁,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台地四时和暖,冬无霜雪,亦无酷暑,但大风之日多,无风日少,春日常旱,秋多水潦。”(97)如台湾恒春县,“沿海一带,平时则有落山风,凡田园中枝干锐上之物,均不能种,夏秋又有台飓,其祸更烈,望之可以丰收之岁,顿成灾歉。”(98)特别是台湾地区处于太平洋地震带,地貌变化较大,水土流失也较为严重,也造成农业生产规模的萎缩。有载:“地多震动,水浮石稀,土不坚实,若种植五谷,虽与中土同,而一年惟秋季一收,阻饥之患所不能免,幸有薯芋之类,足以果腹。”(99)类似的生态条件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人们必须依赖生态环境获取生活资料,而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常常制约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人类依赖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如何更好地利用生态环境为人类服务,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时期,差异很大。一般而言,当人类生产力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人类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对生态环境改造力度则较大。反之,只能够受制于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开展低层次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活动。华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活动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注释:
(1)《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2)《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3)《嘉庆广西通志》卷八十七《舆地八》,光绪补刻本。
(4)[清]朱仕王介:《小琉球漫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
(5)[清]徐怀祖:《台湾随笔》,丛书集成初编本。
(6)《嘉庆广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二《关隘略》,光绪补刻本。
(7)[清]张庆长:《黎歧纪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8)[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五《风俗》,《台湾府志三种》,中华书局1985年。
(9)《噶玛兰厅志》卷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10)《宋史》卷二百九十四《苏绅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809页。
(11)《舆地纪胜》卷一百一十五,江苏扬州古籍刻印社1993年。
(12)《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七十八《列传二十三》,光绪补刻本。
(13)《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七十九《列传二十四》,光绪补刻本。
(14)[清]屈人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376页。
(15)[日]奥田或《台海蕃人の烧农业》,《农村经济考》第一辑,昭和八年版,第193页。
(16)《广西富川县富阳区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编。
(17)《环江县玉环乡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编。
(18)《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19)[明]顾山介:《海槎余录》,《国朝典故》卷一百零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6页。
(2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一辑,台湾故宫博物院1978年,第160页。
(21)《道光长乐县志》卷六,《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22)《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7页。
(23)《瑞岩民族学调查的初步报告》,《文献专刊》第二号,1950年。
(24)[清]唐赞衮:《台阳闻见录》,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25)[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26)[清]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五,《台湾府志三种》,中华书局1984年。
(2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28)[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国朝典故》卷八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27页。
(29)《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台湾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582页。
(30)[清]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广东民族研究所1983年编,第280页。
(31)《民国海南岛志》第三章,《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第二册,上海书店2001年,第114页。
(32)[清]黄叔王敬:《台海使槎录》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33)[清]邓传安:《蠡测汇钞》,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5页。
(34)《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
(35)宋兆麟:《我国古代踏犁考》,《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36)[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37)[元]王祯:《农书》卷十三《觑拭拧罚万有文库本。
(38)可参阅李衍垣:《贵州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39)《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五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40)[清]张庆长:《黎歧纪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41)《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42)《道光琼州府志》卷三,《中国地方集成·海南府县志辑》第一册,上海书店2001年,第36页。
(43)《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44)《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09-110页。
(45)张一民:《白裤瑶乡见闻录》(续),《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集,广西师大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2000年编印。
(46)[清]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
(47)《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五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48)《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一十九《列传二十四》,光绪补刻本。
(49)[清]华本松:《百色志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50)《嘉慶广西通志》卷二百一十八《列传二十三》,光绪补刻本。
(51)[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四,辽沈书社1991年,第432页。
(52)[清]沈起元:《治台私议》,《台湾理蕃文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53)《台东州采访册·疆域》,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54)《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二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456页。
(55)《台湾舆地图记·埔里六社舆地说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56)[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57)《道光琼州府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第一册,上海书店2001年,第35页。
(58)[清]华本松:《百色志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59)[清]魏祝亭:《两粤瑶俗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八帙。
(60)《嘉庆广西通志》卷八十七《舆地八》,光绪补刻本。
(61)《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蠻夷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0页。
(62)《嘉靖南宁府志》卷十一《杂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8册,中国书店1992年。
(63)[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四,辽沈书社1991年,第413页。
(64)[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65)[清]六十七《番江采风图考》,丛书集成初编本。
(66)《噶玛兰厅志》卷五下,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67)《嘉庆东莞县志》卷九,《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68)《嘉庆广西通志》卷八十七《舆地八》,光绪补刻本。
(69)[清]黄叔王敬:《台海使槎录》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
(70)[清]朱仕王介:《小琉球漫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71)[宋]朱辅:《溪蛮丛笑》,《说郛》卷五,中国书店1996年。
(72)[清]张庆长:《黎歧纪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73)《噶玛兰厅志》卷五下,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74)[清]黄叔王敬:《台海使槎录》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75)[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丛书集成初编本。
(76)《民国琼山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第三册,上海书店2001年,第270页。
(77)[明]顾山介:《海槎余录》,《国朝典故》卷一百零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9页。
(78)[清]朱仕王介:《小琉球漫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
(79)《广西侗族自治区凌乐县后龙山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5年编。
(8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81)[清]张庆长:《黎歧纪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82)《嘉庆广西通志》卷九十《舆地十一》,光绪补刻本。
(83)《广西僮族自治区西林县那劳区那兵乡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
(84)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
(8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537页。
(8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辑,故宫博物院1978年,第494页。
(87)[清]赵翼:《碫曝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48页。
(88)[清]郁永河:《稗河纪游》,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89)[清]郁永河:《番境补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89)[清]林谦光:《台湾纪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91)《嘉庆广西通志》卷八十七《舆地八》,光绪补刻本。
(9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5824页。
(93)[清]张庆长:《黎歧纪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94)[清]吴振臣:《闽游偶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95)[清]沈起元:《治台私议》,《台湾理蕃文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97)[清]吴振臣:《闽游偶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98)《恒春县志》卷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
(99)[清]林谦光:《台湾纪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