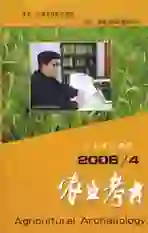试论中国传统农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
2006-11-24黎康
黎 康
如何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史界一直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而在这一研究中,朱熹理学无疑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不过,海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还只是罗列和整理了朱熹理学体系中所包含的与自然科学知识相关的诸多内容(如: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生物等等学科的具体知识),而缺乏对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细致而深入的论说,尤其是缺乏基于宋代科技思潮背景下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对朱熹建构其理学体系产生影响的具体分析与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对宋代科技思潮整体效应的把握,从范畴、方法、价值这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农学对朱熹理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地剖析,以期对深化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与视角。
一、“久处田间,习知穑事”
朱熹(公元1130——1200)生活于古代科技勃兴的宋代(1),受科技思潮的影响颇深。他在博览群书,广注经典,致力于经、史、文、乐、佛研究的同时,对《黄帝内经》、《灵宪》、《正蒙》、《梦溪笔谈》和《新仪象法要》以及历代的天文、历法、音律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典籍也同样用力甚勤,其中尤以对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沈括所著《梦溪笔谈》,更是倾注心血、研读精详,并对书中所载诸多科学观点作了亲自验证,有的甚至作出了自己极富创见的阐发。在吸收和阐发前人科学思想的同时,朱熹还亲自参与和从事了一定意义下的科学考察和探究活动。如:在古田杉洋地下就挖出了朱熹夜观星象的聚星台、石室等遗址(2);他还家藏浑仪,热心恢复苏颂发明的水利传动装置(3);而且还曾尝试用木自制过“华夷地图”(4)。与推崇“验迹”“原理”科学方法的沈括一样,朱熹也是一位注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5),他之所以能在古代天文学、生物学及地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凭借的就是“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与“身到足历”(以览山川之势)的功夫。其所获取的科学成果充分体现了“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结合”(6)。由此可以肯定:朱熹确实是一位足以代表时代水准的自然科学的热心关注者和探究者。农学知识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其当然也在朱熹的关注(“俯察”)之列。正如他自己所说:“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7)
除了探求自然科学知识的个人兴趣之外,朱熹之所以关注乃至研究农业科技,更多的还是出于他为官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农业的繁荣与儒家所倡导和憧憬的“仁政”、“德政”息息相关。如孔子就将“足食”和“先富后教”作为德政的要素;孟子也以发展个体农民的“制民之产”作为“仁政”的主要内容。这种将农业与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由孔孟开其端绪而渐成儒学的“主流意识”。作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朱熹,自然秉承了“农政合一”的传统;况且,朱熹所处的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将“劝课农桑”作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出于从政的现实需要,朱熹对农业生产也必须加以重视。宋淳熙五年(1178年),由于朝廷重臣史浩的推荐,朱熹被派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于次年三月底到任。南康之地本已是地瘠民贫,而当时又值旱灾发生。为此,朱熹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另一方面深入田间地头研究和分析农事、民情。他说:“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窃见本军已是地瘠税重,民间又不勤力耕种,耘耨卤莽灭裂,……所以土脉疏浅,草盛苗稀,雨泽稍愆,便见荒歉,皆缘长吏劝课不勤,使之至此。”(8)所以他要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朱熹在知南康军以及后来为地方官期间,深刻地体会到了农业对于“民生日用”的重要性:“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9);他还说:“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亻卒皆以劝农为职。……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10)可见,农业是民生之本,劝农是为官之职,这是朱熹积极体察农事、研究农业科技的根本原因所在。
朱熹所处的宋代流行一种新型的公文形式——“劝农文”,它是宋朝地方官员于每年春耕将兴之时所发布的劝民耕种的榜文。与宋代之前的农书相比,由于“劝农文”直接针对的是本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情况与特点,故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它采用文告的形式写成,通常篇幅较小,文句亦简练,因而便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劝农文”的最基本的职能便是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朱熹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思想就主要体现在他任地方官期间所颁发的若干《劝农文》及有关的榜文之中。其中,尤以宋淳熙六年(1179年)十二月在南康军颁发的《劝农文》和宋绍熙三年(1192年)二月在漳州(今福建漳州)颁发的《劝农文》较为重要。朱熹的《劝农文》往往是在农事的关键时候为劝导农民不误农时尽力务农而颁发的官方文告,由于其中既有农民必须遵照执行的条令,也包含了应当如何操作的具体方法,因而也多少反映出一定的农业科技思想。通过对朱熹《劝农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农业自战国以来就形成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深耕细耙,改良土壤;其二,适时播种,不务农时;其三,多施基肥,适时追肥;其四,加强田间管理;其五,注重兴修水利。尽管朱熹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思想只是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劝农文》之类的官方榜文之中,显得缺乏整体性,但他毕竟对农事作了一番体察与研究,而且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如耕种、施肥、插秧、除草、轮作、灌溉、丝麻等等)(11)。
朱熹穷其一生致力于理学体系的建构,从其思想的成熟演进历程来看,朱熹生平学问经历了三次总结:第一次是淳熙四年丁酉(1177年)。从寒泉之会经鹅湖之会,再到三衢之会,由此促成了《四书集注》的诞生,而《四书集注》的首次序定就成为朱熹学术思想史上划分前后半生学问的界碑;第二次是以淳熙十三年(1186年)写成《易学启蒙》为起点,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次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得已完成。这次总结是在论战中得到完成的,它标志着他的《四书集注》的理学体系臻于成熟;第三次总结发生于庆元三年至庆元五年(1197—1199年),他把经学著述的重心转到了《礼》学和《尚书》学,由此建立起了他的“五经”学。由此可见,朱熹那两篇重要的《劝农文》以及他的理学著述是相间完成的。应当说,朱熹后期著述受“久处田间,习知穑事”这段体察农事经历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况且,破落世家出身的朱熹是在寄人篱下中长大的,“从小亲于农事”(12),对于“稼穑之理”有着相当真切的了解。在《朱子语类》中就常常有朱熹以农事喻“理”的记载(如他以“园夫灌园”来比喻“读书之法”(13))。朱熹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少年时的这段经历应该是会有所影响的。当然,朱熹始终是把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放在首位,而且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朱熹实际从政的时间也并不长,“累计方逾七年”(14);因此,从朱熹理学体系整体构成来看,其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思想至多只能是居于次要和从属的位置。不过,在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体察与对农学知识的掌握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完善和精制理学。虽然中国古代农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与思想基础)还无法从整体上对朱熹理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其从范畴、方法与价值等诸多层面还是对朱熹理学所呈现出来的某些思想特征与面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15),而宋代科技思潮所致力的从“无常形”现象之后寻求“常理”(即规律)的致思趋向,无疑就是这一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表现。这种“求理”精神渗透于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宋、明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就,不仅在军事(火药)、航海(指南针)以及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字印刷)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正是在创研这些具体科技成果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探求和追寻“阴阳相感”与“阻碍相通”之“常理”的兴趣与热情得到了普遍而有效的激发,从而汇聚成蔚为壮观的宋代科技思潮。这也就是生逢其时的理学家们“并不缺乏科学倾向”(16)的真实原因之所在。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其所参与和从事的所有科技探究活动,都毫无例外地打上了宋代科技思潮影响的烙印。正因为朱熹能以一个足以代表时代水准的自然科学探究者的学识去进行哲学思维和体系建构,因此,自然科学对理学所产生的影响就可以经由朱熹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而达到,而范畴(还有方法乃至价值取向)就成为这一影响过程得以完成的中介。事实上,朱熹关于“理”为“自然之理”(规律)的理解,就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与进步的影响而被凸显和强化。具体而言,其首先就得自于对沈括《梦溪笔谈》所提供的诸多自然科学成果与材料的吸取与整合。
“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无所不通”的沈括,正是在广泛而深入的科学探究基础上,提出了“大凡物理有变有常”的命题,主张从实际观察和实验中去获取材料和数据(“验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类求故,概括出一般原理,以揭示“此理必然”(“原理”)。利用“验迹”“原理”的科学方法,沈括从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对“理”作为“自然之理”(规律)进行了详尽的探究与考察,其涉及“声律之理”、“共鸣之理”、“磁石之理”(物理学)、“造算之理”(数学)、“胎育之理”、“用药之理”(生物及医学)、“雷震之理”(气象学)等诸多方面。作为科学家的沈括,其所考察和揭示的“必然之理”实际指的就是具体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而于“天文、地志、兵机,亦皆洞究渊微”(17)的朱熹,以“理”范畴为中介整合利用了沈括对“自然之理”(规律)探究与考察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和思想材料,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朱熹深研过沈括的《梦溪笔谈》,认为“沈存中博览,《笔谈》所考器数甚精”(18),这就使得力倡“泛观博览”的朱熹,能够更加专业而有效地吸取和利用沈括的科学成果来为理学服务。如朱熹在阐述关于日月星辰之“理”时,就吸取和利用了沈括关于日食月食的科学成果,并明确指出:“唯近代沈括所说乃为得之”,其“足破千古之疑”(19);再如朱熹在与蔡季通探讨“声律之理”时,肯定了沈括对此的理解,他说:“琴固每弦各有五声,然亦有一弦自有为一声之法,故沈存中之说,未可尽以为不然”(20);关于潮汐涨落之“理”,朱熹也赞同沈括的观点,认为“沈存中《笔谈》说亦如此”(21)。正是由于朱熹“取法于沈括之处颇不少”(22),故此使“理”在朱熹处能以事物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意涵出现。朱熹对“理”作为“自然之理”(规律)的理解,同样还得益于宋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影响。宋代农业生产水平相当高,尤其是朱熹所处的南方。一批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科技方面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如陈沟摹杜┦椤贰⑶卣康摹恫鲜椤贰⒃乐止的《禾谱》、曾三谨的《农器谱》、范如圭的《田夫书》以及毕功绩的《水利图经》等。这些著述涉及到农业科技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宋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3)。农业科技与天文历法等一样,是与政治的需要(皇权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政合一”)。正因为农业科技在古代社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度曾沉浮于仕途宦海的朱熹,也自觉地关注为政之本的农业及农学生态知识。他“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因此对“稼穑之理”有一定的体察与了解。正是在这种身体力行的体察中,“理”之作为“自然之理”的意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与凸显。朱熹说:“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24)。对于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季节时令,朱熹认为其变化是有规律的,他说:“天地之运,春夏秋冬,莫非道理”(25);而农业生产就必须按照时令节气变化的客观规律来具体安排,他说:“草木亦有理存焉。……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26),这与成书于公元1149年偏重于讲“农事之理”的“江南农学专著”——《陈古┦椤匪强调的“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27)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农业是人与天直接打交道的领域,因而“天人”之间的矛盾是农业生产的产要矛盾,对此,朱熹一方面强调了人力的作用,认为“用力勤,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28);另一方面朱熹也强调了要“顺理”、“顺性”即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他说:“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29),“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具体而言,就是要“取之以时,用之以节,当春生时不夭,不复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丛林。”(30)显然,这样的结论(即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对农业生态(“稼穑之理”)进行详细体察之后才能得出。
作为朱熹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理”既是形而上之本体,也是普遍的存有根据,更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同时,“理”又广泛地包括“造化”“名物”“度数”“礼乐”及各种事物的具体规律。总体而言,“理”在朱熹处有二重意涵:其一,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其二,是“所当然而不容己者”。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31)。这里,所谓“所以然”即是指决定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内在本质与规律(“物理”);而所谓“所当然”则是指规范人的行为活动的各种准则,主要是指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性理”)。可以说,“理”作为朱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与逻辑始点,它既是理论思维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知识与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由于范畴一方面具有超越不同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参与和承载不同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潜入性,这一特性使范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与哲学交互影响的中介(思想载体和思维工具)。“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32)。朱熹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吸取、利用与整合正是基于范畴的上述特性。当然,要使内在的影响过程得以完成,还必须具备广泛性的知识背景和个体的专业知识结构,而朱熹正是在实际的科技探究活动中使二者契合,故此,“理”作为“客观规律”和“事物本质”的意涵才能得到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揭示与阐发。
三、“穷天地鬼神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
“万物皆有理”,这可以说是北宋思想家们如张载、二程、沈括、陈沟热嗽谌鲜蹲匀弧⑷鲜渡缁峁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从“万物有理”这一观念出发,经由自然推及到社会,进而上升为“至理”“天理”,这是理学创立初期理学家们思想发展所共同遵循的基本思路。因此,不管后世理学家们对“理”作何解释,理学在创立之始确实是无法脱离自然界中那个实实在在的“物”。也就是说,要体认作为理学最高范畴的“理”,其最为现实的途径便是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加以认识。如二程就说:“物理须是要穷”(33),“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显,必有所以然者”(34);“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35);“‘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36)农学家陈雇ü对农事的亲自考察(“躬耕西山”)也得出结论:“天地之间,物物皆顺其理。”(37)朱熹秉承二程“格物穷理”方法论的基本思路,并结合自己对农业、农事的体察与认识,也指出:“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38)可以说,宋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不仅拓展了朱熹“格物穷理”方法论的适用范围,而且使研究与掌握农学知识和农业科技也成为了“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朱熹所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39)
必须指出的是,朱熹“格物穷理”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于探究“鸟兽草木之理”(“必然之理”),而是希望通过“闻见之知”的获取、积累和贯通,由此去感悟和体认超自然的“天理”——封建纲常伦理(“当然之则”)。他说:“格物穷理,……穷到最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个道理。事君便遇着忠,事亲便遇着孝,居处便恭,执事而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40)这也就是说,探究“一物所具之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体悟那“天下公共之理”。那么,如何从“一物所具之理”体悟那“天下公共之理”呢?这就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所要解答的问题。在他看来,“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此可以推而通之也。”(41)也就是说,由于“一理”分而为“万殊”,“万殊”归而为“一理”,通过类推,就可以“脱然贯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42)的境界。
所以说,朱熹主张格“草木之理”除了要获取“草木”的具体知识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求从“草木之理”(特殊存在)类推出“人伦之理”(普遍有效),换言之,朱熹利用农学知识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类推出人的社会伦理属性及其意义。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他把植物的各个部分与人的各种品德联系起来,他说:“仁是根,恻隐是根上发出的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枝叶。”(43)在《朱子语类》中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朱熹所有关于“鸟兽草木之理”的议论应该说都是建立在对自然之物的一定的观察基础之上的的一种经验性的描述,由于朱熹主要不是对自然之物的结构与功能感兴趣,而主要是以此来说明“人伦之理”(科学知识伦理化),这样无疑就限制了对“自然之物”的认识范围以及认识深度,也就是说,只选择能体现某种道德观的自然现象去加以认识,而且,对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也往往以比附人的某种道德品质为终点,由此相关的类比有时就不免流于随意和粗浅。如他说:“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蝼蚁统属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后,便有兄弟,犬马牛羊成群连队便有朋友。”(44)将动物的本能行为及特征与人的社会性品德相类比就显得相当肤浅。当然,有的借用还是比较精当的。譬如朱熹利用农学知识来阐释理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其“格物穷理”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理一分殊”就是一个范例。
“理一分殊”最早由理学家程颐提出。他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说“《西铭》明理一分殊”。对此,朱熹借题发挥道:“《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逐句浑沦看,便是理一;当中横截看,便见分殊”(45)。为了更好地说明“理一分殊”,朱熹曾直截了当地延用禅宗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遂与如来合"来解释“理一分殊”,并称赞“那释氏也窥得见这些道理”(46)。尽管朱熹对华严宗、禅宗思想多有吸纳,但对其所主张的“一即一切”则多有批评,认为其只讲理的“一多”而不讲理的“分殊”。因此,朱熹自己常常借用“一种万实”来作比喻:“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各各完全;各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47)如果说用“月映万川”来说明“理一分殊”还残留有佛禅的影子的话(“本体论”),那么,当朱熹用“一种万实”来说明“理一分殊”时则更体现了理学作为正统儒家的自身特色(“本源论”)。“理一分殊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中有深远渊源,不能归结为来自佛学”(48)。可以说,朱熹借用“一种万实”(在生命的循环过程中果实遗传有种子的所有生物学特性)这个比喻更准确地表达出了其“理一分殊”的思想精髓,而这只有对“草木之理”相当通晓的人,才能如此娴熟地借用农学、动、植物学知识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和主张,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沉溺于章句的陋儒、腐儒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四、“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
“崇道而贬技”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实例便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9)显然,在主张“君子不器”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孔子看来,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引包氏所言:“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北宋刑的《论语注疏》也说:“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而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这些解释都是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乃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学稼”与“成德”无关。然而,不管后世如何解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包括农业科技在内的科学技术确有贬抑之意。因为,在传统儒家那里,科技知识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有当其具有一定的伦理属性时才有意义。正是在这一价值取向之下,与伦理道德相比,科技就只能是沦为“雕虫小技”。虽然孔孟都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但正统儒家的“重农”思想只是重在“劝农”(“使民以时”(50)),而不是“务农”。虽然从表面来看,传统儒家一方面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又对士人务农加以鄙视,这中间似乎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然而,细究起来就可发现,由于儒家主张“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1),因此,具体到农业而言就体现为:“重农”才是“大人”(“劳心者”)所要“操心”之事,“务农”就只能是“小人”(“劳力者”)所要“出力”之事;重农的重点在于“劝”,务农的关键则在于“力”。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下“社会分工”的需要,所以儒家不得不对士人务农加以鄙视;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又不得不劝诫农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可见,重农与反对士人务农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构成内在抵牾,相反,反而凸显了儒家的价值观。那么,朱熹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他说:“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法,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52)所谓“许行‘君民并耕之说”可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许行主张贤君“与民并耕”,对此孟子以社会分工的道理加以反驳,并且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朱熹把“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君民并耕”对应起来,以说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孟子反对许行“君民并耕”是同样的道理,所依据的仍然是社会分工(所谓“君子”与“小人”、“劳心”与“劳力”的分野)的不同。应当说,朱熹的这些见解总体上并没有超越传统儒家“崇道贬技”的窠臼,不过他同时对这一价值观的历史性存在也作出了一定的辩解。
从朱熹理学的整体性倾向而言,朱熹虽然对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加以了广泛的吸取与利用,但同时他“重德轻智”(重修养轻认知)的态度与价值取向也同样是非常鲜明的。朱熹理学体系的要旨一言以蔽之就是“革人欲,复天理”:“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53)他在《答陈齐仲》的信中就曾这样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等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54)所以,在朱熹看来,学问仅仅对那些以实现自身之“圣”为唯一追求的人来说,才有其价值和意义;所谓“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这都是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论说的;至于人们通过对外在的自然界和工艺制品(“一草一木”、“器用”)加以认识所获得的知识,那是算不上甚么学问的。这也就是说,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自然界进行科学观察并获取知识。朱熹在对“教”与“技”所作的比较判断上也体现出同一倾向,他说:“凡世儒之训诂辞章,管商之权谋功利,老佛之清静寂灭,与乎百家众技之支离偏曲,皆非所以为教也。”(55)可见,在朱熹看来,文艺、事功、佛老之学、百家技艺皆非德教,它们的价值均在德教以下。那么,何谓“德教”呢?朱熹认为:“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5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按照封建道德原则与等级制度的要求去规范,以合乎“圣人”所期望的那样,这就是德教。秉承了传统儒家衣钵的朱熹同样认为“道德教化”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而文艺、事功、技艺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而这样片面抬高德教地位的结果,就必然导致对包括农业科技在内的所有“技艺”的轻视。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对于“技”“道”之间的价值判断其前后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据学者陈来考证,上引《答陈齐仲》的信是写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57),换言之,被后世学者广泛引征用以证明朱熹“崇道贬技”这段议论是朱熹早年(36岁)所发,而学界普遍认为朱熹思想成熟于40岁左右(58),而且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59)。从朱熹个人经历及其理学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的演进历程看来,朱熹以下的说法可以作为他对待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在内的自然科学技术与知识的基本态度,他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60)这是朱熹在注解《论语》中子夏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61)时所作的评论,他的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无疑与他“为学”和“从政”的实践密不可分(尤其是与他“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对农业生产实践和对农学知识的深入体察、了解和利用有关)。当然,朱熹的这一价值取向也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有关。朱熹所处的宋代,统治者对以前的农学成果非常重视,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命令校勘《四时纂要》、《齐民要术》,并镂版刊行;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又下诏颁布农书于郡县。朝廷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农学著述的产生,作为封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朱熹的价值观也必然受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所左右。另外,自然科学日益昌明所彰显出来的在反对宗教蒙昧主义、虚无主义中的巨大价值,也使同样以反对“释老”为学术旨归的朱熹主动对自然科学知识加以充分地吸收和利用,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加以探究已远远超出其个人兴趣与爱好的界限,而完全是出于应对佛老挑战、自觉地复兴儒学传统的理论需要。可以说,朱熹的这一价值取向在一定意义下可视为是他对儒家传统“崇道贬技”价值观的一种“修正”。事实上,朱熹在其一生中的最后十年(AD1190——1200),也即60至70岁时,他在科学研究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而这无疑是其个人价值观前后发生改变的一个最好佐证。
五、结语
中国传统农学和中医学、天文学和数学一道并称为中国古代最为发达和完备的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四大学科体系。从《吕氏春秋》刊载我国最古老的农学论文《上农》及《任地》、《辩土》、《审时》等诸篇起,作为理论形态的农学由此就踏上了知识化演进的历程。汉代的《汜胜之书》可以说草创了我国古代农学体系,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本形态,而与朱熹几乎同一时期的《陈古┦椤纷魑综合性农书又呈现出“求农事之理”的新格局。可以说,在朱熹建构理学体系之前,作为知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农学已经成型。当然,中国传统农学对朱熹理学的建构究竟有没有产生过影响以及产生过何种影响,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与朱熹理学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的重要门类之一,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成为了朱熹建构其“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理学体系的重要知识来源、基础和背景之一。朱熹作为一名儒者和官员,他获取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及农学知识的途径有二:其一,从中国传统历代典籍(尤其是儒家早期经典)中间接获取。如《诗经》、《楚辞》及《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尔雅》中就包含有许多“鸟兽草木之名”和农学知识,这些知识朱熹通过对经典的广泛注释完全能够学习、了解并获取;又如朱熹还详研过沈括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从这一反映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综合性科学著述中,他所获也颇丰;另外,对于前朝和本朝的有关农学著述,朱熹也有可能涉猎:如他在写给朋友陈胜私(克己)的一首诗中就曾提到自己想“青灯彻夜课农书”(62)。其二,从农业生产实践中直接获取。出于从政(履行地方官职责)的现实需要,从小就“亲于农事”的朱熹还直接参与并从事了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实践,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超出技术常识范围的深入体察与了解,而这一“久处田间,习知穑事”的亲历过程,无疑为朱熹获取中国古代农学知识进而对其建构理学体系产生具体影响搭起了一座得以沟通和实现的桥梁。
(2)中国古代农学得以实现对朱熹理学的影响,从学理层面分析其主要得益于以范畴、方法、价值三者为中介。就“理”范畴而言,朱熹基于对农业生产实践的体察与了解,而充分肯定了“虽草木亦有理存焉”,这在一定意义下是肯定了“理”作为“自然规律”的存在,这也就使“理”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达到了同时代科技思潮所能达到的水平;就方法论而言,由于受沈括“验迹原理”科学方法的影响,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论并不排斥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和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而且将认识“草木鸟兽之宜”看成是体认“形上之道”的必要途径。尽管朱熹对农业生态知识的运用有时显得随意和肤浅,但有的借用却显得非常精当,如他利用农学知识“一种万实”(全息遗传)对“理一分殊”的阐释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鲜明特色;从价值观上看,传统儒学一直是“崇道而贬技”(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便是这一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然而,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日益昌明、传统农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农业在现实政治生活及“民生日用”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朱熹亲自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体察和了解,使他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为“小道”存在的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下是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一种“纠偏”。
(3)朱熹理学受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这是朱熹理学能够摆脱宗教形态、发展理性思维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之一。当然,我们不能随意夸大这种影响的存在,因为朱熹建构理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探究自然现象、追求自然知识,而是为了弘扬儒家伦理、为封建道德寻求理论根据,也就是说朱熹理学的意旨始终是为了对封建等级制度下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不可移易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为道德论提供宇宙论基础)。所以,朱熹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的诸多吸取与利用,其真实的目的就在于为完善和精制理学体系服务。虽然,一方面由于朱熹广泛地吸取与利用了包括农业科技知识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完善理学体系,使之更趋于精制;但另一方面,由于科学(“创新”)与理学(“守旧”)的“精神本性”迥异,所以,朱熹越是能以一个足以代表时代水准的自然科学的探究者的身份来建构理学,其体系的内在矛盾越是无法避免,这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大抵晦庵(朱熹)之论佳处很多,然窒碍之处亦不可毛举”(63)的根源所在。
注释:
(1)宋代自然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87页。
(2)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3)据《宋史·天文志》四十八卷载:“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另,《语类》卷二十三也有“楼上浑仪可见”的记载。
(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朱文会尝欲以木作《华夷图》”。
(5)(英)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6)(英)斯蒂尔·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简称《语类》)卷四十九。
(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
(9)《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
(10)《文集》卷一百,《劝农文》。(11)有关朱熹的农业思想可参见程利田:《从(劝农文)看朱熹农业思想》,见《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乐爱国:《朱熹的农业科技思想与理学》,《朱子研究》1999年第2期。
(12)束景南:《朱子大传》(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4页。
(13)《语类》卷十载:“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园夫灌园,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间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
(14)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1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页。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17)(宋)黄干:《行状》。
(18)《语类》卷九十二。
(19)《楚辞集注·天问》(20)《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
(21)《语类》卷二。
(22)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载《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24)《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
(25)《语类》卷四。
(26)《语类》卷十八。
(27)(宋)陈梗骸杜┦椤ぬ焓敝宜篇》。
(28)《文集》卷九十七,《劝农文》。
(29)《语类》卷七十五。
(30)《语类》卷十四。
(31)《大学或问》卷二。
(3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0页。
(33)《程氏遗书》卷十五。
(34)《程氏粹言》卷二。
(35)《程氏遗书》卷十八。
(36)《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37)(宋)陈梗骸杜┦椤ぬ焓敝宜篇》。
(38)(41)《语类》卷十八。
(39)《语类》卷六十二。
(40)《语类》卷十五。
(42)《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43)《语类》卷一一九。
(44)《语类》卷二十四。
(45)《语类》卷九十八。
(46)《语类》卷十八。
(47)《语类》卷九十四。
(48)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49)《论语·子路》。
(50)《论语·学而》。
(51)《论语·里仁》。
(52)《语类》卷四十三。
(53)《语类》卷十三。
(54)《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
(55)《中庸或问》。
(56)《中庸章句》,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57)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58)“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37岁),确立于已丑(40岁)。”见陈来:《朱熹早年思想研究》(上),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
(59)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6页。
(60)《语类》卷四十九。
(61)《论语·子张》。
(62)《文集》卷七。陈克己(胜私),据考为农学家陈怪子,朱熹在知南康军时,他曾携农书见朱熹,供其“赈荒劝农之用”。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63)李冶:《敬斋古今黄主·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