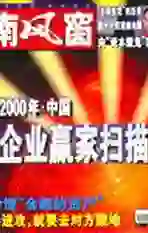珍惜“会跑的资产”
2001-06-14■秦朔
■秦 朔
 电子邮箱里来了封国内邮件,是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发的。他曾在中国彩电业的著名公司创维工作,后来跳槽到一家同行那里。邮件里说创维最近“高层地震”,原营销负责人陆强华被创维老板黄宏生弃用,加盟昔日对手“高路华”,尾随他出走的营销人员有上百人。他的疑问是:创维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爱多”?
电子邮箱里来了封国内邮件,是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发的。他曾在中国彩电业的著名公司创维工作,后来跳槽到一家同行那里。邮件里说创维最近“高层地震”,原营销负责人陆强华被创维老板黄宏生弃用,加盟昔日对手“高路华”,尾随他出走的营销人员有上百人。他的疑问是:创维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爱多”?
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太清楚,也不想“就事论事”,只能鼓着“旁观者清”的勇气,根据在美国对人力资源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谈几点看法。
怎样看“出走”?
在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里,“出走”不是个褒义词。公司有人出走,要么是公司的责任,管理不善,前景黯淡;要么是出走者的原因,缺乏忠诚,见异思迁。总之,人们大多把公司有人出走看成一个不正常的问题。国内有的知名企业甚至动用公安机关去捉拿出走的员工,老怕人走了,就是什么“家丑”。而媒体一听到“出走”,本能的反应就是某某企业出毛病了。
美国企业界也有过对“出走”不宽容的时期。特别是东部那些制度森严的大公司。但随着硅谷文化渐渐成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主流,员工的流动性已经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积极涵义。硅谷的公司把高流动性看成在硅谷经营的一种成本,这种成本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现在我们都知道,硅谷之所以成其为硅谷,决定性的因素是企业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先进性。如果论科研实力和风险资本,美国东部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比硅谷条件更优越,为什么硅谷后来居上了呢?
柏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两个地方作了比较。在他看来,东部的公司像DEC和DataGeneral等都是自给自足型的帝国(Self-containedEmpires),人们只对自己的工作、公司有兴趣,不刻意增加外边的人际网。东部公司认为“跳槽”难以接受,更偏爱资深职员,公司晋升凭借的是良好的内部关系,而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获得成功。离开DEC的雇员往往被视为“贱民”,一旦与“母教”脱离关系就别想再回来。在128号公路地区,稳定和忠于公司较之实验、敢于冒险更受重视。当地的科技企业所效仿的也是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的结构,所有小公司的目标都是成为老牌大公司,它们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大公司,摆出一副大公司的架子,着力于建立“小而全”及垂直一体化的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在企业发展之初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和组织稳定,可是越往后,它就越是妨碍企业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缺乏横向信息交流压抑了实验和学习的机会,传统的公司结构限制了管理积极性和技能的发挥。在和硅谷的竞争中,128号公路地区终于由开始时的领先落到了下风。
而硅谷的整个企业系统则是开放的、分权的、更倾向于不断催生新公司的。有人称之为“创造性的解构”,有人叫它“权力分散型系统”,有人甚至把硅谷本身看成一个大的“分权的公司”。这固然是因为硅谷的公司在地理上非常接近、易于建立频繁的非正式交流,但更深的原因在于,硅谷最为崇尚的是尝试的自由、创业的快乐和对技术创新的兴趣,而对东部企业的繁文缛节和“办公室政治”毫不感冒。硅谷先驱们创建的企业,组织松散,类似由工程师组成的合作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硅谷就以知识和技能在本地工业团体间的扩散速度见长。各个公司的工程师们在酒吧里交换意见、传播信息,经营者们也逐渐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甚至是一些流言蜚语里发现极有商业价值的一面。信息交换也存在于正式工作中,正如一位硅谷人所说:“竞争者之间相互交流,这是我们的文化。如果一个领域中遇到困难,我会毫不迟疑地给另一位执行总裁打电话询问。尽管我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但他肯定会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硅谷悖论”,竞争需要不断创新,而创新反过来又需要公司间的合作。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内在的忠诚及对优势技术的共同协议把本行业的成员团结起来,它们都在竞争市场份额和技术领导地位,但同时又都依靠这个地区独树一帜的合作。
硅谷独特的文化使其成为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区(10%到12%),活跃的人才流动使人们有机会学到更多新知识和专业技能,建立起广泛的人际网,成为未来再创业的基础。硅谷最宝贵的财产是人,所有公司都用慷慨的奖金、股票期权、高工资和有趣的项目,吸引顶尖人才。但遇到员工离开公司寻找新机会,也能够得到公司许可,如果不成功还能回来。当然,地理位置上的接近确实为工作流动提供了便利,“这儿的人们换了工作,连车位都不用换。”在持续不断的员工出走和企业改组中,职业忠诚和友谊通常能存活下来。有公司主管这样描述,“硅谷的网络超越了对公司的忠诚。我们公平地对待员工,他们对我们忠诚。但还有更高层次的忠诚,即对网络的忠诚。”“有很多人早上来上班时认为,他们在为硅谷工作。”
在硅谷这种开放、流动、刺激冒险、竞争又合作的背景下,“员工出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1957年,因不满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的独断倾向,8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出走肖克利试验室,成立仙童公司。这8个人又称“8叛徒”(TraitorousEight),在硅谷人心中,他们代表的是光荣。摩尔、葛洛夫等人在60年代末又出走仙童创业,这才有了英特尔。如果硬要说“出走”就是叛徒的话,那么硅谷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叛徒文化”。只不过硅谷人对叛徒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识大相径庭。Sun公司CEO(首席执行官)麦克尼利就说,他以Sun培养出多少位CEO自豪而不是悲戚。
 让广东“硅谷化”
让广东“硅谷化”
以上述介绍为背景,依我看,创维人才出走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广东电子消费品产业能够领全国之先,和丛林式的布局、适合创业的制度环境、对人才流动的开放心态是大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广东能够在今天的中国工业版图上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拜市场化的制度所赐。广东哪一个名牌企业没有吸收过同行精英?哪一个企业的人才不是经常出出进进?看看广东企业每年在招聘广告上花的钱就知道了。有那么多位置要招人,既有企业扩张的需要,更有人员流动造成的空缺。从某种角度看,职业经理人频繁的来来往往,恰恰说明了广东企业整体生长环境的成熟。人是可以流动的,便于流动的,公司间对人才流动的心态是正常的,建设性的,这种环境才有利于新企业的诞生和发育。在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壁垒之间,通过人才流动带动了知识、信息和管理技能的流动,使得每个企业的知识集成能力始终处于动态的更新状态中。有更新,有学习,企业才不会停步。
硅谷只有一个,但硅谷文化谁都可以借鉴。在美国,犹他州和亚里桑那州致力成为“硅漠”(SiliconDesert),德州奥斯丁一带要作“硅丘”(SiliconHills),纽约是“硅道”(SiliconAlley),西雅图和波特兰是“硅林”(SiliconForest)。硅谷精神无处不在,也就是所谓“makemeanywhere”。比如,微软所在的西雅图现在有超过2000间软件和互联网公司,和硅谷一样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竞争又互补的“丛林式”格局。
在广东今后的产业发展中,如何保持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如何创造企业间活跃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环境,如何更好地鼓励新创中小公司的发育,是值得业界和政府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作为媒体,面对企业人事变动等问题时,也应该有一颗平常心,不要为了炒作而给企业形象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广东的“硅谷化”进程,有赖多方努力。创维人才出走,也许双方有些恩恩怨怨,但我认为,看远一步,都不是什么坏事。我对黄宏生的企业家才能和陆强华的职业经理人素质都非常尊重,相信他们能够以高度的眼界和未来观,超越事情本身的得失,收获生命的感悟与清醒,走向明天。我愿意设想的未来是,创维经过这场人事风雨赢得了企业自身再调整和再出发的机会,创造新辉煌。而陆强华也在又一个舞台上再次证明了职业经理人的价值与作用。
“唯一的财产”
倡导对人才流动持宽容心,不等于不重视人才。相反,正因为人才是一种“会跑的资产”,而且是能动性很强的变量(不好好使用和训练,人会成为企业的包袱,资产变成负债),所以如何发掘人力资源,发挥人力资源的价值,实在是21世纪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过去几百年里,企业最稀缺的资源一直是金融资本,也就是钱。如今,金融资本不再稀缺,现在公司最感匮乏的是人力资本——才能、知识和创造力。这是新的稀有资源。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出过一本特辑,《21世纪的公司》,核心观点就是,21世纪的经济是创造力经济(CreativeEconomy),创造力是财富和成长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唯一的财产(asset)。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精英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个有创造力的知识精英,其所创价值胜过许多一般性劳动的总和。我在美国的一位指导老师的侄子在3M工作,他说公司有一整套激励“goodidea”(好的创意)的办法,如果你的某个idea被公司采用了,你可以立即休一年的假,到世界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旅行,而该产品将来产生的利润,你还有一份。我在《哈佛管理评论》上看过一篇访问迪斯尼公司董事长艾斯纳的文章,他说迪斯尼最重要的管理任务是“管理梦想”,即怎样保护和激发创作设计人员的梦想。微软2000年25周年庆,时代华纳公司出了一本纪念专辑,由微软上上下下很多员工亲自写感受。我翻了几篇,深深感到微软员工对公司的那种自豪和热忱,这正是微软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不惜投入的结果。比尔·盖茨在这本书里写到:“我们从没改变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雇用聪明的人。这没有任何替代品,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容易……我们会全身心地去发现合适的人……一旦你选定了最好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信任他们。从一开始,我就是依靠别人的思想和经验来支持我自己的,很多时候,他们填补了我知识中的空白。我们把员工分成小组,赋予他们权力去塑造我们的产品形象,提供他们所需的技术和资源,帮助他们完成工作。我们给他们成功的机会也允许他们失败,只要我们从他们的错误中学到了东西。当然,我们也给他们机会去分享他们帮助创造的成功。”
对人力资本的评估正在成为美国一些顾问公司的新业务。和对一条生产线、一块厂房的拥有状态不同,即使公司在法律意义上是员工的雇主,但他仍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支配自己的人力资本。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怎么干,他有很大决定权。公司当然可以靠制度来监督员工,但一方面,监督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创造力的喷发可能是监督的产物吗?
硅谷的人才流动性很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硅谷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也最活跃。硅谷是创造性劳动之谷,是美国最普遍运用期权制度的“利益共同体”之谷。期权制度不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全部,但却是一个基本前提。《南风窗》刊登过一篇《硅谷不眠夜》的文章,描述硅谷人夜夜加班的敬业场景。如果公司资本和自己的人力资本之间没有一种直接的利益统一关系,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吗?
在21世纪这个知识驾驭物质、人比钱更重要的世纪,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再造,都必须花大力气解决好人力资本的培育、激励和管理的大问题。WTO涛声在耳,时不我待,千万不要让“会跑的资产”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