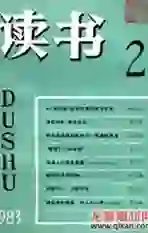重读《西线无战事》
1983-07-15朱雯
朱 雯
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把《西线无战事》看完。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董老对《西线无战事》(Im Westennichts Neues,一九二九)的评价,虽然只有十分简短的一句话,却是世界公认的一个不刊的定论。从董老接着所写的几句话里:“不钻入人的生活的深处,不能写小说,要多懂点社会情况,人情世故,宜多看小说”,①不难看出,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一八九八——一九七○)的这部小说,好就好在那是作者“钻入人的生活的深处”之后写出来的。
是的,《西线无战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雷马克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从学校直接报名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五次负伤,特别是最后一次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从火线救出一位受伤的战友时,在英军的突然袭击下,自己被好几颗手榴弹所炸伤,伤势相当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总算只在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伤痕。这段经历,便是他创作《西线无战事》的生活基础。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这部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仅仅花了六个星期,他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却在抽屉里搁置了六个月。一家书店不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另一个出版社总算把它接受下来了,先是在《福斯报》上连载,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连载的时候,那个报纸的销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十九世纪英国读者争先抢购狄更斯连载小说的盛况,居然重见于德国。一九二九年一月全书出版以后,更引起了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轰动。仅在德国国内,第一年就销售了一百二十万册。同年三月,首先被译成英文,每册定价虽高达七先令六便士,但六周之内也销售了二十七万五千册。把其他许多语种的译本一并计算在内,总发行量当在五百万册以上,这在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意外的成功,使原先是个无名小卒的记者,竟然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有的人喜爱他,有的人憎恨他,有的人称颂他,有的人低毁他,一时间对他本人和这部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一向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既不愿意接见为此而来访的客人,更不愿意参预有关他作品的争论,而且他从来都以“不问政治”自居,不料到了一九三○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采取反对英雄主义的态度,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在军事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正是锤炼国家社会主义的钢铁精神的熊熊烈火,因此他们怎么也不能宽恕他对这个纳粹神话的挑战。正好那时由《西线无战事》改编摄制的美国电影准备在柏林某剧场放映,纳粹党魁戈培尔便利用这一时机,唆使一帮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向那家剧场进行破坏和捣乱,迫其停演。这一行动,迫使雷马克不仅离开柏林,而且离开祖国。他后来说,“一九三一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到了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开烧毁,随后又因为他坚决拒绝回国而于一九三八年被褫夺了德国国籍。雷马克虽已流亡国外,但是纳粹政权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一九四三年,他那住在德国的胞妹埃尔芙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说她不相信德国会取得胜利)被纳粹法庭判处了死刑。
在雷马克一生所写的十一部作品中,《西线无战事》是他的成名作,从创作思想、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来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因为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起,一切都已基本上定型,后来的发展是很不明显的。
我们说《西线无战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而决不是一部自传。它完全不受具体历史事实的约束:它描写战争,既不指出时间,也不标明地点,更不接触到具体的个别的战役,例如凡尔登战役或索漠战役之类;它只写了一连串作战的进程,甚至只写了机枪、大炮、飞机、炸弹、坦克、毒气等等,而很少写到敌军的人员和对方的活动。正是这一点,使这部小说不同于当时其他许多描写战争的作品,而赢得了历久不衰的成功和众口一词的称誉。
作为一部小说,《西线无战事》的故事本身非常简单。作品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用第一人称)和他的同班同学阿尔贝特·克罗普、米勒、勒尔,在校长坎托列克的沙文主义宣传的煽动下,报名当了志愿兵。在部队里,这四个人又跟锁匠恰登、泥煤工海伊·韦斯特胡斯、农民德特林和斯坦尼斯劳斯·卡特辛斯基(简称卡特)结成了好友。小说就是写这八个普通士兵在西线战壕里的生活以及对这场战争的感受。全书十二章,每章都以一系列动人的情节描写了战壕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可独立成篇,综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表现了作者对战争的全部观感。
在《西线无战事》的十二章里,雷马克着重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作者笔下的战争,既没有堂皇的军容,也没有壮丽的场面,有的只是毒雾硝烟,断肢残骸,以及战壕中的血泊,胸壁上的脑浆,树枝间的肠脏。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在《战城南》中也写过“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的诗句,虽然同样感动人,但那毕竟是诗人的想象,而雷马克所描写的则是亲身的经历,目睹的真实。特别是作者笔下的战士,既没有“保卫祖国”的崇高行动,又没有决死疆场的英雄气概,有的只是捉虱子,打老鼠,烤小猪,偷白鹅,长官折磨兵士,兵士作弄长官,有时还用军粮面包去换取占领区女人的“爱情”。他们时刻担心着被打死,就仅仅为了要保全自己,才不得不去杀死别人。就这样,这些涉世不深、天真未凿的青年,“对于人生的知识仅只限于死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这些有时还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描写,目的决不在于描写本身,更不象有的评论家指责的那样在于投合时好,而是在于揭露战争的罪恶。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即将爆发,德国的政治斗争日趋激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甚嚣尘上,他们扬言德意志帝国并没有被战胜,而只是由于国内爆发了革命,战争才遭到了失败。纳粹党徒更竭力鼓吹要从战火中锤炼英雄,在战争中效忠卖命。因此,雷马克用这种方法来描绘战争,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心灵创伤,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严重摧残,戳穿了统治者所编造的关于“英雄”的神话,就当时来说,无疑地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小说虽然只写了八个普通兵士在西线战壕里的生活和在后方的经历,但是战争给予大家的痛苦、灾难和创伤,他们一致认识到,“这在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儿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呵。”是的,这一代人,“他们即使躲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这一代人,其实也就是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等作家自己所属而又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迷惘的一代”。对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这一代人的归宿,小说主人公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而且,人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因为在我们之前成长的一代,虽然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年,但是他们都早已成家立业,现在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战争就会被忘掉,——而在我们之后成长的一代,象我们从前一样,跟我们完全陌生,将会把我们推在一边。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将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有些人将会适应,还有些人只是顺从,而绝大多数人将会茫然不知所措;——岁月流逝,我们将归于毁灭。”
残酷而恐怖的战斗生活,并不妨碍,甚至反而会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在沼地营房接受军训的时候,博伊默尔常常奉派担任看守俄国战俘的任务。在黑暗中,他看见他们黑黝黝的身影,看见他们在夜风中飘动的胡须,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对他们,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俘虏,可是为什么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会成为俘虏的呢?敢情是:
“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仇敌;一道命令说不定又会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有某几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人签署了一项文件,于是多少年间,从前一向受到全世界鄙视和最严厉处罚的罪恶,便变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
又有一次,为了要侦察敌军阵地,博伊默尔匍匐前进,到了敌人的散兵线后面,躲在一个大弹坑里窥测,忽然有个法国兵沉重地摔了进来,他不假思索,就用枪刺往那人身上戳去。眼看着这第一个被他亲手杀死的人——一个名叫吉拉尔德·杜凡尔的法国印刷工人艰难地死去,他再一次进行了紧张的思维和痛苦的探索:
“……在从前,对我来说,你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活在我心里、引起适当反应的抽象的东西。正是这种抽象的东西,我用刀刺去了。可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到你是象我一样的人。以前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步枪;现在我却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庞和我们的伙伴关系。饶恕我吧,伙伴。这种事情,我们总是发觉得太晚了。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是象我们一样的穷鬼,你们的母亲也象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而且我们也一样地怕死,一样地会死亡,一样地会受苦——。饶恕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
“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类似的问题卡特也提出过,他说:“……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来这儿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无怪恰登要问:一场战争究竟是怎么会发生的?卡特认为“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除了皇帝和将军们以外,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譬如说,“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的工厂老板都成了大富翁。”这个结论是对的。雷马克让他作品中的人物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可是从这个结论,他并没有再往前走下去,没有能使他的人物进一步探索改变这种不合理现实的途径,没有能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就象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在他的小说《火线》(Le Feu,一九一六)中所描绘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了人民革命,当时不但在俄国,不但在匈牙利,而且在雷马克的故乡德国,革命的烈火都已经燃烧起来了,可是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里没有作出应有的反映,相反地他在作品中倒是尽情渲染了所谓“伙伴关系”和“战友情谊”,企图以此来与当时的黑暗现实相对照,从而维护所谓人的永恒价值。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塑造的人物只能是受难者、牺牲者,而不是反抗者、战斗者;他们看不见前途,找不到出路,只是相信偶然,听凭天命。这也不能不使整个作品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大大地削弱了揭露与批判的力量。素以“不问政治”自居、力求置身于政治之外的“中立主义”者雷马克,他的政治局限性在这里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西线无战事》这部成名作,不仅为雷马克的创作倾向定下了基调,而且也为他的艺术手法开创了风格。雷马克的艺术风格是独特的:文笔那么简练,比喻那么贴切,讽刺那么辛辣,抒情那么动人。特别是小说的结构,貌似松散,实际上环环紧扣,串串相联,有些地方还看得出作家在材料的组织与安排上费过不少心力。有的评论家认为《西线无战事》从头至尾只是一连串可怕的场景和阴惨的气氛,其实也并不尽然。作家非常巧妙地顺着故事发展的进程,在可怕与阴惨中间往往穿插着欢乐和快意的情节,有时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插曲。例如有一次,博伊默尔和卡特到团部一所棚屋里去偷鹅,卡特望风,博伊默尔翻过墙去动手,一对白鹅已经捉在手里,却没想到一头猛犬扑将过来,把他逼倒在地,好容易他拔出手枪,发了一弹,那狗闪到一边,总算让他来得及把鹅抛到墙外,自己登上墙头,翻到外面,跟卡特会合,两个人胜利回营,把鹅烤好后请大家饱餐了一顿。(跟这个插曲同样滑稽可笑的是,有个名叫尼克尔的纳粹评论家居然拿这个情节来攻击雷马克,说他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一方面,对战马受伤,呻吟野外,表示强烈抗议;而另一方面,宰杀白鹅,烤而食之,自己却行若无事。因此,有人就讥刺这位评论家,说道这个尼克尔不但是个国社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象这一类有趣的插曲,在作品中俯拾即是。
《西线无战事》那貌似松散的结构以及往往包含着许多哲理的隽永的对话,给读者一个印象:这部作品好象是个剧本。这一点,雷马克自己也承认。当有人问起他写作成功的关键时,他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想当剧作家而没有成功的人。……我的所有作品写得都象是剧本。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在雷马克看来,创作不是一件乐事,而是一件难事,他常常认为最容易的还是写对话,而读者也确实认为他作品的主要力量正好在于锋利的对话。他在这方面的写作技能,雷马克曾经自己声称,应当主要应归功于他那双“爱好音乐的耳朵”。他说,“我是用耳朵写作的。我听到自己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我凭音乐选择词语。因为我是爱好音乐的,因为我曾经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风琴手,因为我的确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我的小说被高声朗诵的时候,听起来总是很悦耳的。写对话,别的作家感到最困难,在我倒觉得挺容易。”
《西线无战事》从最初发表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长期以来,在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也遭到各种恶毒的攻击。有个化名为埃米尔·马里乌斯·雷克瓦克(Emil Marius Reguark)的人,写了一本进行嘲弄的模拟作品,书名为《特洛伊城墙前无战事》(Vor Trojani-chts Neues,一九三○年柏林版),也用第一人称,说他的唯一目的只是要在战争结束以后发一笔大财:“我将成为一个富翁,全希腊都会谈我的作品。”还有一个扎洛莫·弗里德伦德尔博士(Dr Salomo Fried-laender),化名米诺纳(无名氏Anonym的倒写),写了一篇题名为《真有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其人吗?》(Hat Erich Maria Remarque wirklich gelebt?一九二九年柏林版)的恶毒谩骂文章。甚至在雷马克逝世以后,《泰晤士报》有个名叫伯纳德·利文(Bernard Levin)的专栏作家,还在文章里把雷马克说成是“连第二流作家”也排不上,说他的《西线无战事》“比写得不错的黄色小说稍微好一些”。所有这些诋毁、谩骂和嘲弄,都丝毫无损于雷马克这位作家和他的这部作品的光辉存在。历史已经、而且还将证明,《西线无战事》这部雷马克的成名作,将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载入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史册。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部作品决不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而就作家本人来说,这本书也决不能代表他的最高成就。
(《西线无战事》中译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①见《读书》一九八一年第十期154页。